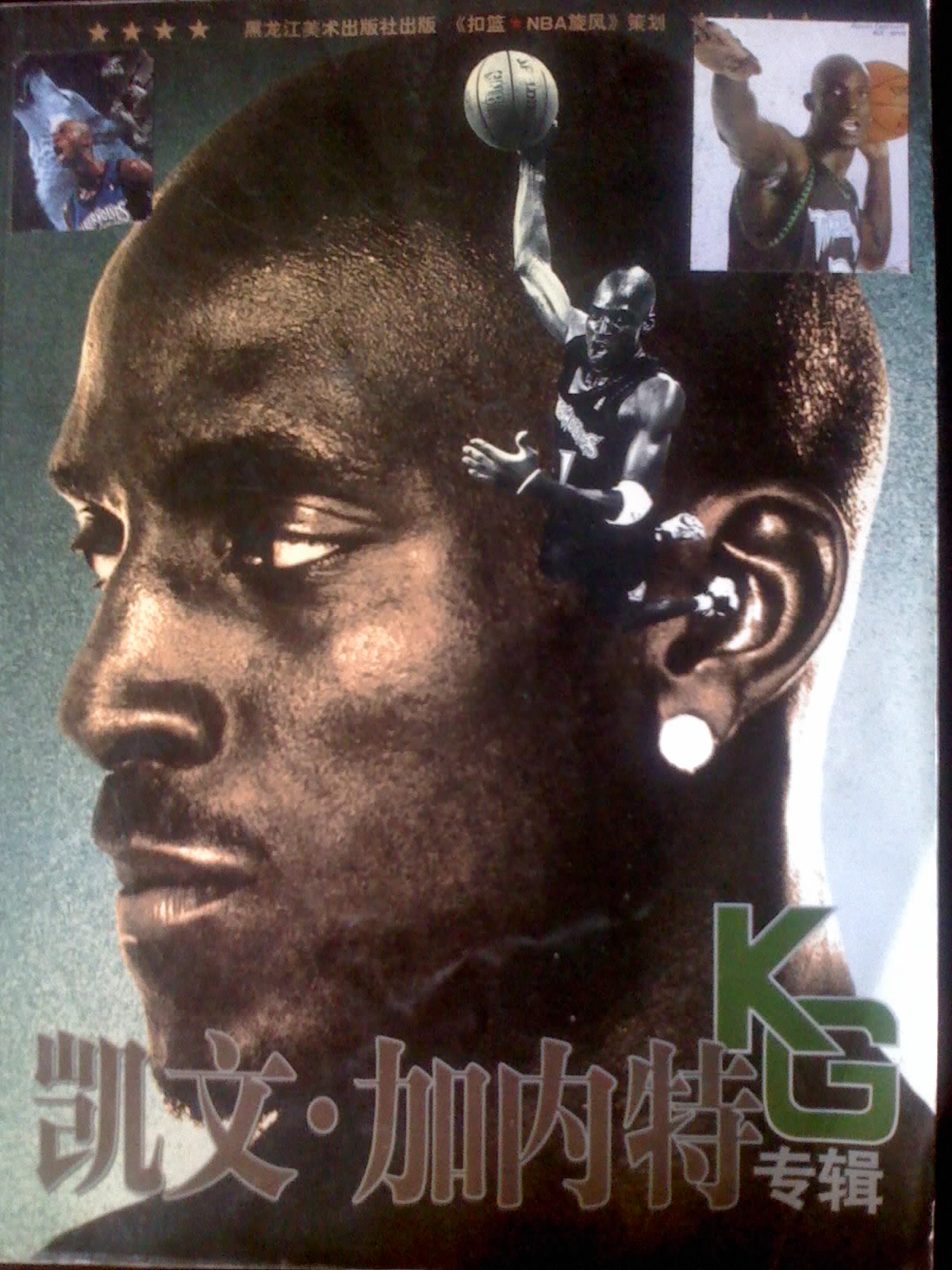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打开APP
怀念那段网吧的岁月,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网吧(来自猫扑)
引子
北京也无非是这样,北三环的网吧满座的时节,望去确也有人才济济的模样,但座间也缺不了推着小车到处叫卖的服务员穿着制式的T恤,操着河北某地的口音,每呼喝一句总要将最后一个字先拔上去,还要将尾间扭几扭,颤一颤,实在标致极了。
双安旁边的地下室配置鼠标键盘不久前都换了,虽则价钱贵一点,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包间倒也还可以和异性网友视频一番的。但第到下午放学或包夜时段,大区的一些座上便常不免要嘿嘿嗬嗬地吼得震天,兼以豪气干云旁若无人;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曰:“那是在打山口山(即魔兽世界)。”
你就往郊区去。出了西四环,不久就了一处集市,旁边还有一处民办学校,号称“东方大学”。你坐在一处忘记名字的偏僻网吧里,这里的系统还是Win98,一些机器的内存只有128M,耳机有33%的几率一边不响,屏幕上脏不拉叽地蒙着一层灰。一些人在义薄云天地联CS,一些人在嘤嘤嗡嗡地玩着等几种老掉牙的网络游戏,另一些人则在QQ上跟异性或者不知道什么性的网友眉来眼去。这里多数换气扇没有打开,屋内烟熏雾绕,混上流通不畅的厕所的异味,让人鼻孔堵得慌。在这样封闭的环境里呆上几个小时,你的头发、衣服上全是烟味儿,毛孔被堵得油腻腻的,眼睛发酸,喉咙发苦发涩最后发痛。你开始感到不适,很快你重新适应了曾经熟悉的环境,然后心安理得泡起网来。
因为之前的几年里,你所熟悉的典型网吧环境一直都是这样的。
网吧与少年
当我还未满18岁的时候,网吧还没有限制18岁以下人士进入,但是那时网吧 还在用Modem上网,收费颇为不菲,消费得起的人年龄多半都在18周岁以上,而当时18岁以下人士多半也还不晓得有网吧 这样一个娱乐场所;在我年满18周岁的多年以后,“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相关措施”,限制18岁以下人士进入网吧等娱乐场所。这个时候,大家进网吧上网就要掏身份证登记并验明正身;这个时候,我已经“两鬓苍苍十指黑,乡音无改鬓毛衰”,但网吧服务员仍然坚持我出示相关证件,不出示能证明我身份的证件,就不让上网,我只好费力地从钱包里翻出即使半夜里被 联防队员拦住也没有用到过的身份证;旁边有粗心的人递上了临时借来的身份证,服务员照登不误……我猜,你和我一样,身份证最大的用途就是云网吧自己上网或者借给哥们儿上网,因为成天用身份证坐飞机飞来飞云的人实在不大会有兴趣来看这本杂志……
但是有时候,也能在北京 的网吧里看到一些身穿肥大校服的少年。这多半在下午放学时间,一些身穿肥大校服的年轻男女结伴而至,到处找寻连在一起的座位。坐下之后,就一色地开始往WOW的服务器上联。间或也会有人退下来联几手CS,或者有人事急,先告退,不过多数时间里他们在坚定而安静地玩WOW。一般而言,不会有人留到晚饭时间,一般一到两个小时,这、些年轻人又会像他们 来时那样结伴安静地离开。如果网吧里没有人在吵,他们也不会吵,我估计这是一种北方式的礼貌,因为在四川的中学生在网吧里实在太喳闹了,所以我禁不住总要拿他们云跟这些安静而有礼的年轻人比较。即使是夏季,他们也穿着那种肥大的运动服式校服,这种校服以抹杀女生身材而恶名昭彰。
没有问过他们是怎么能登记上网的,也许他们都 是高三学生,已年满19岁准许上网,不过有时候你能很明显地从骨骼、肌肉和皮肤看出旁边的中学生并没有年满18岁,也许连16周岁都没有。实际上,即使未满19岁,也完全可以绕开身份证上网。在北京市区的大多数较大型网吧,用30元(或50元,当然,这不是重点)和一张身份证就能办到一张会员卡。所以审些年轻人完全可以借一张身份证来办张会员卡,然后一劳永逸地绕开18岁问题,当然前提是他们的长相不要太嫩。我在北京的两年间确实没有在网吧里见过看上去明显未满16岁的小孩子,太嫩的面相,即使借到身份证也不管用。曾经有一个外地口音的小伙子 在网吧里找我借身份证好去办包夜,我拒绝了,因为他面相太嫩,一看就只有16岁上下,如果按我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计算,他不是天赋异禀,就是驻颜有术。当我需要带未满 18岁的小朋友一起来上网,无非也是这套-把我的会员卡借给她,自己则用身份证登记上机。
所以在北京的网吧里,始终没有见到年龄明显低于18周岁的小孩在上网,即使有,也是一些再过一两年就满18的高中生,不过,从来没有在包夜时看见过他们 。这一点上,北京做得比较好。当我还在成都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小孩子呆在网吧里,不过那是在2003年1月以前。成都的中学生去网吧都不怎么穿校服,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群背着书包看起来既像大学生又像中学生的人结伙走进大学外头用民居改建成的小网吧 ,大声问老板还有没有空机子,然后,在座位上大声地同隔壁屋的同伙汇报当前局势。当他们联CS联得入神,夹杂着兴奋的粗话的吆喝声会突然从隔壁屋里响起来,那是在欢呼某人连爆4个头或在最后一秒拆掉的丰功伟绩。除了周末,他们一般也在放学时间出现,不会呆得太久。放暑假后,网吧里的中学生就多起来,或者单打独斗地在网游里练级,或者成群结伙地包夜联CS。大概成都的网吧管理比较松,2001年在北京和武汉的网吧上网,都已经需要出示身份证,然而我记得在2003年以前,成都的中小网吧是不怎么需要出示身份证的,所以那时这些中学生可以畅通无阻地溶入Internet的宏大海洋中去。
更早之前,我在成都街头巷尾的小网吧里遇到过一些年纪更小的访客,这是一些小学生。因为没什么钱,他们总是先把钱交给网吧老板,然后一起联,当时间一到,老板就催他们下机走人,这些小孩多半会用尽办法拖延时间,一直到老板把他们从座位上拖下来,才恋恋不舍地走出网吧回家去。比较大型和正式的网吧虽然也很随便,但一般不接待这么小的客人。
200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看见两个最多才上初一的小孩走进成都一环路东一段的一家网吧他们的旁边是一群正在变声的初中生和一个剃光头的中年人,这些人正在快乐地联着CS ,光头中年人看上去心肠颇好,就带小孩玩CS。打着打着有人往人群里扔闪光雷,两个小孩不知道躲闪,屏幕一片惨白,不清楚出了什么事,还大呼小叫:“老板!显示器坏了!” 中年人就教导说,遇到闪光雷就要把头(游戏里的头)扭过去。后来又有人往人群里扔闪光雷,在爆炸的一瞬间,这两个小孩把眼睛一闭脖子一扭,而屏幕依然一片惨白。根据前武汉某网吧资深网管车冬明的《网管日记》记载,当监察队来到他工作的网吧检查时,找不到身份证的人们出示了五花八门的证件来证明他们 已经年满18周岁,这些证件有:户口本、大专毕业证、退伍军人证,下岗证,其中显然车冬明认为最富幽默感的,是一个使用结婚证的家伙。就我推测,这个家伙可很可能是基于如下推理来使用结婚证的:“已知女人比电脑远为先进和贵重,所以一个已经结了婚、知道该在女人面前负起什么样责任的人,同样也知道在电脑胶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过我估计监察队的人可能不太懂,因为他们是监察队。
网吧与通宵
成都的春天……龙泉的桃花烂漫的季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双结队的年轻男女,卿卿我我,还要将胳膊互相缠上。川大周围的几家电脑游戏房有几个好玩的游戏可打,有时还值得去转一转。但是到半夜,学校周围总有几间民房的窗户 不免要灯火通明,兼以满房大呼小叫;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打星际。” 实际上,很多人一提到网吧,想到的就是通宵。早在1997年和1998年,成都各所大学的背巷里还满是不能上网,只能局域网联线打游戏的电脑游戏室,它们统统号称“网吧”,这个时候通宵活动就早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当时我还在川大,男女生恋爱成风,很多仍是单身的男性大学生不得已都把目光转向了游戏,经常有整个整个的寝室在周末结伙去只能打游戏的“网吧”通宵联或“红警”或“三角洲特种部队”。这样,一到周末这些 “网吧”的机位总是十分紧张,甚至需要预约。后来出来了,又是全国山河一片“联”,大家都通宵钻研秃鹫车战法和叉子兵rush.
后来网吧兴起,大家都咸于冲浪,鉴于上通宵总比按小时计费要便宜,自诩有着国防身体的大学生们自然比较倾向于打通宵,这不仅由于经济原因,还有着之前从电脑游戏室时代延续下来的身体惯性和风俗习惯。通宵很少见到中学生,因为他们还要上学,不到周末是断然不肯结伙跑到网吧里来打通宵游戏的,到现在也一样。
当时大学周围的大学里头的网吧里,90%以上的都是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偶尔会有一些社会青年 ,但是他们在那时犹如坐图书馆一般的上网氛围必定不会感到自在(当时大学里的网吧大多氛围都较好,大概学生把上自习和泡图书馆的习惯带了进来罢),于是又匆匆地走掉了。1999年11月和12月,我和两个朋友在川大西校区一个叫科教网吧 的地方上网,作息时间是这样:19晚上时起床,互相打传呼聚众吃饭,吃完后去网吧坐下,一直坐到次日早上八九点,然后一起去川大红河谷吃包子,吃完去街机厅耍KOF,花两块钱买七八个币,耍到11时各自回寝室睡觉,睡到19时又起来……这种作息时间保证了我们具有连续通宵的人能力,据其中一个朋友所述,之前的10月他就玩了30个通宵。其间我们经常能在网吧里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所谓“熟”就是白天在街机厅里也经常看得到的。那时我的身体还很健壮,冬天里能在连续两个通宵之后(中间不睡觉)淋个冷水澡去跑3000米,后来因为通宵太多身体每况愈下,真是恼火得很,所以没事不要瞎通宵。有一回就在网吧里,我们看见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在网吧门口打着电话,忽然就靠着门板向后滑倒,脸色铁青。知道的人说这个通宵太多,连续玩了15天,中间几乎没怎么睡觉,才搞成这个样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板们纷纷开动脑筋,有的在网吧里安放可折叠的长沙发,一些行军床则折叠起来放在门背后,另处一些地方大的网吧干脆拿出一间屋子来让大家睡觉。我见过的最大的睡觉间有4张双层床,理论上可以容纳8个人,实际不可以容纳12个人睡觉-他们让两个人挤一张下铺。临到毕业时,有一个叫李强的生工系同级熟人经常睡在一个网吧的双层床上回寝室睡觉,毕业后我又去过一个那个网吧,李强已经做了该网吧网管,每个月支300元的薪水。2000年初我常去川大外磨子桥路口的一个二楼网吧,在那看见几个似乎在玩UO的小伙子,看上去跟老板颇熟,而且好像就住在网吧里,因为无论何时我去那个网吧,总能看到他们各据一台电脑在PK或者被PK。2002年春节我又去了那间网吧,令我完全说不去话来的是那几个家伙还呆在那里,他们 看上去是那个网吧除我以外有且仅有的顾客,他们还在玩那个游戏。从口音判断,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不是成都人。然而他们 看上去已经在网吧定居,并溶入了老板一家去了--他们跟老板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一起吃午饭,沙发完全摊开,上面几条凌乱的被子……这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
通宵时也在网吧看到发羊癲疯的。2001年暑假我在成都一环路上的一个网吧里通宵,一个电子科大的学生1时走进网吧来想要打发时间。他看见我在玩“星际”,就建议单挑两三局以消磨时间。我还在攒兵,他的手突然伸过来打翻我的键盘,然后蜷缩着滑倒在地上,吐白沫,抽搐,眼角上沾着不知哪来的泥土。120急救车到了之后,他也醒了,拒绝去医院,要记录学校姓名,也拒绝了,问是否初发,回答以前没有过,然后很快走掉了。我估计他是害怕学校知道他有病。之后我再也没有在网吧里看见发羊癲疯的,那种奇观我确实还想再看一次。
在北京,靠近大学的网吧,通宵的都是一些不打游戏手就痒的大学生。离学校越远,网吧里的成分就越复杂。很多个深夜你可以看见一些使用劣质化妆品的、二十来岁的妙龄女郎在网吧里进进出出,当然会明白是怎么回事;有时她们深夜来到网吧,说明她们才起订,或者刚做完一笔买卖,有时她们深夜离开网吧,说明她们接到了单子,或者要回家睡觉。网络只是一种便宜的通讯工具。有时候可以看见一些操着外地口音的年轻人,他们多半是附近商场或餐馆的保安或服务员,但有些时候一些外地人完全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上周末在劲松东口的一个网吧里,我听到一些人在讲我们那里小地方的方言,但是我看不来他们是干什么的,只看出他们都比我年轻,在玩着某种很弱智的网络游戏。在这个网吧里我还看到一支队伍,他们的口音五湖四海,还有一个女的,他们在WOW的同一个服务器里组队做任务。天快亮时,一个北京人问:“下周什么时候?周五还是周六?”这些人周五周六地商量了一阵,终于定了时间,就各自回家了。就我推测,这些人只有周末有时间,可见是上班族,大概是一些网友不堪忍受家中慢得要死的网速或老掉牙的机器,于是来网吧通宵组队做任务。
历年所见,在网吧通宵总是男多女少,学生多其他少,大人多小孩少,青年多老头少,弱男(至少看起来弱)多壮男少,没女人的多有女人的少……其实诸多长年累月在网吧通宵玩游戏的男性青年通常都其貌不扬,肢体健壮,精力充沛,缺少异性伴侣,是游戏和网络将他们过剩的精力引导到了对现实世界不存在的事物的意淫上。
网吧与禁令
2002年6月,因为"蓝极速事件",国家曾经一度责令全国网吧禁止通宵营业并整改,那时在成都,大型网吧的通宵都停掉了,他们只从8时开到次日0时,只有一些小网吧还在自强不息地办着通宵.那些通宵的网吧,0时以后外面的大门总是关得严丝合缝,不透一点光线的,若是想进去,得先在门外面对一阵山歌,里头的人恨不得让你报上"义字当头","刀下能生","人生漫长艺术短暂"一类的江湖切口,然后铝门或铁门啪咔打开了一线,等里头的人看清你的面貌,才会让出一个人宽度来放你进去,进去之后,那门就像受惊的贝类,迅速有力地再次合上.
一起通宵的人和网吧老板私下里聊天的时候,也表现出对通宵禁令不久就会放开的信心,认为即使禁令不解除,网吧想要做生意,也总能找到办法,越小的网吧越好想办法。实际上,下达这个禁令的人不会想到,因为惧怕检查,一旦失火,这些小网吧紧闭的铝门或铁门或什么什么门,也将像蓝极速的卷帘门一样,阻挡逃生者的去路。
后来在7月,川大南门外的一家大型网吧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新开始通宵营业,真是坑灰未冷西川乱。开始他们还羞答答地营业一天关一天,说是要应付检查。但是看检查的不来,就索性直接搞通宵。后来风声似乎又紧过一阵子,但通宵终于没有停。
全国每年吸烟致死的人数有120万,相当于48 000个蓝极速,而歌舞厅这种娱乐场所也会失火,死的人比蓝极速只多不少--2000年12月25日,洛阳东都歌舞厅大火死309人,相当于12个蓝极速还多9个人;每年的矿难,死亡人数总有隐瞒,光是2004年一个河南大平矿难,就死了148人。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找出更多。
但是这些行业,都不会出现类似网吧业这样的情形(即使是暂时的)。如果消费档次比网吧高,缴纳的利税也就更多。国家也从来不禁烟,不禁采矿,每年死掉恁多人,烟照卖,矿照采。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烟草业和采矿业每年带给国家巨额的税收,如果网吧业也能带来这么多的税收,那么景遇也会改变很多吧。
初到北京的时候,因为似乎听到检查的风声,网吧们停过一阵子的通宵。但在北五环以外的地方,那些破网吧的“通宵嘉年华”依旧在随着排气扇叶子快乐地旋转起舞,彻夜不眠。到如今终于都松懈了下来,还有几个人记得蓝极速呢,而风头也就过去了。
网吧与“入室盗窃犯罪以及暴力”
中国城市的街道上经常会悬挂一些莫名其妙的标语,比如“严厉打击入室盗窃犯罪分子”。网吧左右也算“室”,所以这标语也适用于那些在网吧偷东西的家伙,应严厉打击之。
在网吧你可以经常看见诸如“提示:请看管好随身物品”的条幅,有的网吧还会在后面加上“……本网吧概不负责”以推卸责任,可以推而知之贼人之猖獗。实际上,我在网吧里从未丢过东西。多年以前,去网吧的时候什么也不带,所以也没什么好丢的;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成天背个包走街串巷,去网吧也带着。当我撇下它去上厕所,或者靠着椅子呼呼大睡进,它从未不见过,被人翻过甚至挪动过。一般来说,在一个有网管随时巡视的网吧里,想丢点东西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职业窃贼不怎么光顾这样的网吧;而你的邻座多半又全身心沉浸在游戏或Internet的世界里,眼里只有显示器没有其它。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2004年夏天我在瑞得在线网上游3楼“刷夜”,有一回在前半夜就睡着了,随即马上惊醒了---一个人正背着光站在我旁边,他看见我 ,就说了几句什么。我听不懂,问他说什么,他又说了几句什么就转身下楼了,这时我看清是一个大约十三四岁,高鼻深目黄卷发的新疆小孩,摸了全身,没丢东西。我问旁边的一个大学生这人是怎么进来的,大学生玩着游戏答非所问地笑着回答,他大概在说什么“找错人”了吧。大约是1时左右的事,这个时候网上游1楼门口刚好没人守着,可见该新疆少年早已不是生客,但与这位新疆少年的缘份,也就一面而已,之前和之后都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
如前所述,很多时候一些风俗业从业者把网络作为一种廉价的通讯手段,但是鉴于他们并不在网吧里高,显然不能算进去。不会有人在网吧里吸毒贩毒,因为网络游戏本就是“电子viper”,这些中毒者已经没有余力去吸第二种viper;也不会有人在网吧里砍人,他们都在网络里砍。一般来说更为常见的一种算不上犯罪但也不是什么好人好事的是网吧暴力,也就是在网里打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网吧里打人或者衩打的几率不会太小,相信读者诸君中心有人亲身体验过。一般来说挨打的原因不外乎作弊,在网络游戏里PK人家外带嘴欠,CS玩得太好外带嘴欠等几个原因。
规模较大的暴力行为,根据武汉某网吧资深网管车冬明所述,是当时武汉一伙玩家,挨家挨户地搜索网吧,看见在里玩道士的不由分说就拖出来打一顿。这些人多半玩战士,对玩道士的玩家保怨已久。当我还在成都的时候,在网吧里被打过,也打过人,在民风温柔敦厚的西川尚且如此,后来流窜到北方,知道北地民风剽悍,一直老老实实上网,战战兢兢做人,还没有被真人PK过,但亲眼所见和听说的网吧真人PK就不下十几起。有一起是朋友所述平日大家熟识的一个胖子,诨号“前田”的,因为CS打得好,在网吧被一伙人怀疑作弊,后来仔细看了,不是作弊,这伙人仍然截住前田,撸走了手表;另一起是同伙的两个人,因为CS进配合不好,互相埋怨,最后发展成用椅子互相真人PK。
最后,就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游戏玩得好嘴又欠,最好还是在家上网,到时就算有人想打你,也得找着人,下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网吧与网吧
如莱布尼茨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完全一样的,网吧和网吧也不一样。有大网吧和小网吧,有明网吧和暗网吧,有学校旁边的网吧和离学校很远的网吧。有电话拨号的网吧和专线接入的网吧……基本上,只要是个网吧,它就和其它网吧不大一样。
早先的网吧,多数是用电话拨号上网。据我以前一个广西朋友所述,他回广西柳城家乡,想找个网吧上网,走进去一看,56K小猫吱吱地拖着7台电脑,6个人正埋头于文字MUD,于是坐下来打开IE输入网址敲回车,6个人猛地回头怒目而视,好像在说“狗日的!又在开网页!”这时网页也都打开了,里头的图片尽是些红叉,原来网速太慢,图片都打不开……又据我以前朋友青×所述,当时川大外头太平路上的“网络咖啡”(其实是两个老板两间屋,外边coffee里面网络,两家互不相干)也是电话拨号一只小猫拖4台电脑,浏览器的缺省设置是不显示图片,而且还要9块钱一小时,当时我也曾打外头经过,依稀记得玻璃窗上的字样似乎是“通宵30元”就没敢进去坐。这都是97年或是98年的事了。
后来,成都的宽带渐渐发展起来了。先是ISDN,128K带宽。在1999年的9月,一条ISDN拖上十五六台电脑依旧慢得伤心,而且还经常断,且不说还有我这样的坏蛋常常背着老板用网络蚂蚁下载摇滚MP3听,这时往往会有在聊天室里跟MM聊得郎情妾意却被网速卡得五内俱焚的男同学跳出来大吼“哪个×人在开蚂蚁?”我就把蚂蚁暂停一下,等他坐回去几分钟,又继续下载……很快11、12月份一些新开的网吧装上了ADSL,这种情况就消失了。当时常常在通宵时先花半个小时下载四五百兆的MP3然后打开Winamp,开始一宿舒服的音乐旅程。
当初去的第一个网吧设在川大西区校医院的一楼,是很安静的所在,每小时3块,通宵12元。当时成都网吧多半是这样:设在一些民居的一楼,如果在街上,则上沿街的一个铺面,一般只有一间屋子十多台机器。最初是下机再结帐,但这样逃单的很多,后来便开始收押金了。我们在科教网吧享受2M带宽ADSL的时候,还是1999年末,当时一个上海网友问这里收多少钱,答10元,于是感叹到处都忒贵,他们那边也是每小时10元,又答曰通宵10元,网友就说大哥你哪个区我马上打车过来,再答曰在成都,那边半晌不做声。到2002年,在成都似乎就看不到在用ISDN的网吧了。天府热线的网吧我没有去过,据说华丽而昂贵。这个时候,感觉成都几乎遍地是网吧,大的小的明的暗的,于是就开始降价,每小时从3块降到两块,再5毛5毛的降,降到某些时段一块钱2小时,降到每天有2~4小时的免费时段……通宵价格也在降,从1999年的12元(还记得我在网络咖啡外头看到“通宵30元”的字样么?)降到10元(这个价格曾稳定了好长一段时间),再降到8元,然后降到6元呀5元,我上过最便宜的通宵是3元,当时半夜摸出去吃碗鸡蛋面也要3元。
2001年夏秋曾经跑过一趟北京,感觉首都就是首都,连网吧都比成都大一点、贵一截,还要登记身份证。当然我说的是那种开在居民小区外头、郭林对面、老家肉饼旁边的规模大些的网吧,五道口的什么“北京技术大学”外边的那种野鸡网吧还是不需要身份证的,但野鸡网吧不提供开水泡面,我们通宵战CS的人只好半夜去对面小卖部买汉堡吃。
接着又去了武汉,协和医科大学外面的大型网吧也要登记身份证,真是全国山河一边“登”。当时需要登记身份证的网吧多半是这个样子:进去首先要经过一个柜台,在那登记并交押金——现在柜台里头几乎都装了隐蔽的摄像头,就正对着你的脸,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然后是一个大间或者几个大间,有时楼上也别有洞天,电脑和桌凳相背着或者相向或者并排或者沿墙壁或者成列成排地整齐列着,这一格局到今天 在很多网吧里也没有多大变化;为了体现安乐祥和的气氛,很多网吧还要放一些音乐,这些歌一般都随网管喜好。当初在北京和武汉他们反复入张学友的Corazon De Melao和周杰伦的《简单爱》,听上去还可以,去年在魏公村的一个网吧,那网管放的歌可真让人酸死了,先是整夜反复入一个什么“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小薇”,后来又开始放《两只蝴蝶》《你好周杰伦》这些歌,因为那里的网管老放这种音乐,我就挪到双安商场附近的一个网吧去上网了。
从武汉回来后我去了重庆,重庆的网吧不要身份证,收费跟成都差不多;过半年回到成都,成都网吧依然不要身份证,真是好山好水好风光。这个时候,蓝极速事发,上头要整风,大网吧目标大,都停了通宵,但川大南站外沿街还有很多十几台20台规模的小网吧偷偷开通宵。我总在一个拐角处的小网吧玩通宵,不仅因为它的显示器比较好,这个网吧总在半夜1时人最饿的时候向客人提供一纸饭盒的热粥,里头掺有炒玉米和小块的泡菜,味道十分好,吃了后半夜很精神。以后我再没遇到过这样充满着终极关怀和人本主义的网吧。当时(2002年夏)的价格是每小时元,通宵6元。现在成都什么样子我不太清楚,每个小时两块钱好像已经多年没有变过,但在北京是不一样的,可以说,首都人民的消费跟首都的政治地位一样高。2004年3月有一阵我居无定所,天天跑魏公村的瑞得在线网上游上网兼睡觉,通宵20,饶是如此,旁边民族大学的学子们还是踊跃报名。春天到了价钱就降了,降到15元。但是网管放垃圾音乐,只好跑去双安旁边的地下室,瑞得在线泰丰宇,一宿收12,这价钱才有点人样。但我依旧要说,12块钱我两年前在成都都要耍两个通宵,而且还有热粥喝,这就是国际大都市的消费水平吗?
泰丰宇的厕所蹲位都拿板子隔开,板子离地大约有30厘米。一回我从厕所出来,遇着一个男的和一个姑娘往里钻,余光瞅着那姑娘也跟着进了男厕所……20000年的成都的一个网吧搞过什么情侣座,一人多高的隔板把两个座隔在里面,四面围住院了三面还多,人一坐进去外面就看不见了,也不开大灯,这种座们我坐进去键盘都看不大清楚,只要你不搞得太响,没人会知道你在做什么。不久之后就被勒令整改,搞了现在那种无隔板的电脑桌,大厅灯一开,一览无遗。
哪也比不上家好
1999年上网到今,大约有2/3的网络时间是在各种网吧里度过的。就我的看法,如果家里安装了宽带,自然是在家里上网最好,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你就是嘴欠一点人家多半也拿你没什么办法。而网吧,一般来说,有恶劣的空气和昂贵的饮食,这且不说,重要的是,这网吧,它不是你的家。
北京也无非是这样,北三环的网吧满座的时节,望去确也有人才济济的模样,但座间也缺不了推着小车到处叫卖的服务员穿着制式的T恤,操着河北某地的口音,每呼喝一句总要将最后一个字先拔上去,还要将尾间扭几扭,颤一颤,实在标致极了。
双安旁边的地下室配置鼠标键盘不久前都换了,虽则价钱贵一点,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包间倒也还可以和异性网友视频一番的。但第到下午放学或包夜时段,大区的一些座上便常不免要嘿嘿嗬嗬地吼得震天,兼以豪气干云旁若无人;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曰:“那是在打山口山(即魔兽世界)。”
你就往郊区去。出了西四环,不久就了一处集市,旁边还有一处民办学校,号称“东方大学”。你坐在一处忘记名字的偏僻网吧里,这里的系统还是Win98,一些机器的内存只有128M,耳机有33%的几率一边不响,屏幕上脏不拉叽地蒙着一层灰。一些人在义薄云天地联CS,一些人在嘤嘤嗡嗡地玩着等几种老掉牙的网络游戏,另一些人则在QQ上跟异性或者不知道什么性的网友眉来眼去。这里多数换气扇没有打开,屋内烟熏雾绕,混上流通不畅的厕所的异味,让人鼻孔堵得慌。在这样封闭的环境里呆上几个小时,你的头发、衣服上全是烟味儿,毛孔被堵得油腻腻的,眼睛发酸,喉咙发苦发涩最后发痛。你开始感到不适,很快你重新适应了曾经熟悉的环境,然后心安理得泡起网来。
因为之前的几年里,你所熟悉的典型网吧环境一直都是这样的。
网吧与少年
当我还未满18岁的时候,网吧还没有限制18岁以下人士进入,但是那时网吧 还在用Modem上网,收费颇为不菲,消费得起的人年龄多半都在18周岁以上,而当时18岁以下人士多半也还不晓得有网吧 这样一个娱乐场所;在我年满18周岁的多年以后,“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相关措施”,限制18岁以下人士进入网吧等娱乐场所。这个时候,大家进网吧上网就要掏身份证登记并验明正身;这个时候,我已经“两鬓苍苍十指黑,乡音无改鬓毛衰”,但网吧服务员仍然坚持我出示相关证件,不出示能证明我身份的证件,就不让上网,我只好费力地从钱包里翻出即使半夜里被 联防队员拦住也没有用到过的身份证;旁边有粗心的人递上了临时借来的身份证,服务员照登不误……我猜,你和我一样,身份证最大的用途就是云网吧自己上网或者借给哥们儿上网,因为成天用身份证坐飞机飞来飞云的人实在不大会有兴趣来看这本杂志……
但是有时候,也能在北京 的网吧里看到一些身穿肥大校服的少年。这多半在下午放学时间,一些身穿肥大校服的年轻男女结伴而至,到处找寻连在一起的座位。坐下之后,就一色地开始往WOW的服务器上联。间或也会有人退下来联几手CS,或者有人事急,先告退,不过多数时间里他们在坚定而安静地玩WOW。一般而言,不会有人留到晚饭时间,一般一到两个小时,这、些年轻人又会像他们 来时那样结伴安静地离开。如果网吧里没有人在吵,他们也不会吵,我估计这是一种北方式的礼貌,因为在四川的中学生在网吧里实在太喳闹了,所以我禁不住总要拿他们云跟这些安静而有礼的年轻人比较。即使是夏季,他们也穿着那种肥大的运动服式校服,这种校服以抹杀女生身材而恶名昭彰。
没有问过他们是怎么能登记上网的,也许他们都 是高三学生,已年满19岁准许上网,不过有时候你能很明显地从骨骼、肌肉和皮肤看出旁边的中学生并没有年满18岁,也许连16周岁都没有。实际上,即使未满19岁,也完全可以绕开身份证上网。在北京市区的大多数较大型网吧,用30元(或50元,当然,这不是重点)和一张身份证就能办到一张会员卡。所以审些年轻人完全可以借一张身份证来办张会员卡,然后一劳永逸地绕开18岁问题,当然前提是他们的长相不要太嫩。我在北京的两年间确实没有在网吧里见过看上去明显未满16岁的小孩子,太嫩的面相,即使借到身份证也不管用。曾经有一个外地口音的小伙子 在网吧里找我借身份证好去办包夜,我拒绝了,因为他面相太嫩,一看就只有16岁上下,如果按我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计算,他不是天赋异禀,就是驻颜有术。当我需要带未满 18岁的小朋友一起来上网,无非也是这套-把我的会员卡借给她,自己则用身份证登记上机。
所以在北京的网吧里,始终没有见到年龄明显低于18周岁的小孩在上网,即使有,也是一些再过一两年就满18的高中生,不过,从来没有在包夜时看见过他们 。这一点上,北京做得比较好。当我还在成都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小孩子呆在网吧里,不过那是在2003年1月以前。成都的中学生去网吧都不怎么穿校服,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群背着书包看起来既像大学生又像中学生的人结伙走进大学外头用民居改建成的小网吧 ,大声问老板还有没有空机子,然后,在座位上大声地同隔壁屋的同伙汇报当前局势。当他们联CS联得入神,夹杂着兴奋的粗话的吆喝声会突然从隔壁屋里响起来,那是在欢呼某人连爆4个头或在最后一秒拆掉的丰功伟绩。除了周末,他们一般也在放学时间出现,不会呆得太久。放暑假后,网吧里的中学生就多起来,或者单打独斗地在网游里练级,或者成群结伙地包夜联CS。大概成都的网吧管理比较松,2001年在北京和武汉的网吧上网,都已经需要出示身份证,然而我记得在2003年以前,成都的中小网吧是不怎么需要出示身份证的,所以那时这些中学生可以畅通无阻地溶入Internet的宏大海洋中去。
更早之前,我在成都街头巷尾的小网吧里遇到过一些年纪更小的访客,这是一些小学生。因为没什么钱,他们总是先把钱交给网吧老板,然后一起联,当时间一到,老板就催他们下机走人,这些小孩多半会用尽办法拖延时间,一直到老板把他们从座位上拖下来,才恋恋不舍地走出网吧回家去。比较大型和正式的网吧虽然也很随便,但一般不接待这么小的客人。
200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看见两个最多才上初一的小孩走进成都一环路东一段的一家网吧他们的旁边是一群正在变声的初中生和一个剃光头的中年人,这些人正在快乐地联着CS ,光头中年人看上去心肠颇好,就带小孩玩CS。打着打着有人往人群里扔闪光雷,两个小孩不知道躲闪,屏幕一片惨白,不清楚出了什么事,还大呼小叫:“老板!显示器坏了!” 中年人就教导说,遇到闪光雷就要把头(游戏里的头)扭过去。后来又有人往人群里扔闪光雷,在爆炸的一瞬间,这两个小孩把眼睛一闭脖子一扭,而屏幕依然一片惨白。根据前武汉某网吧资深网管车冬明的《网管日记》记载,当监察队来到他工作的网吧检查时,找不到身份证的人们出示了五花八门的证件来证明他们 已经年满18周岁,这些证件有:户口本、大专毕业证、退伍军人证,下岗证,其中显然车冬明认为最富幽默感的,是一个使用结婚证的家伙。就我推测,这个家伙可很可能是基于如下推理来使用结婚证的:“已知女人比电脑远为先进和贵重,所以一个已经结了婚、知道该在女人面前负起什么样责任的人,同样也知道在电脑胶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过我估计监察队的人可能不太懂,因为他们是监察队。
网吧与通宵
成都的春天……龙泉的桃花烂漫的季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双结队的年轻男女,卿卿我我,还要将胳膊互相缠上。川大周围的几家电脑游戏房有几个好玩的游戏可打,有时还值得去转一转。但是到半夜,学校周围总有几间民房的窗户 不免要灯火通明,兼以满房大呼小叫;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打星际。” 实际上,很多人一提到网吧,想到的就是通宵。早在1997年和1998年,成都各所大学的背巷里还满是不能上网,只能局域网联线打游戏的电脑游戏室,它们统统号称“网吧”,这个时候通宵活动就早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当时我还在川大,男女生恋爱成风,很多仍是单身的男性大学生不得已都把目光转向了游戏,经常有整个整个的寝室在周末结伙去只能打游戏的“网吧”通宵联或“红警”或“三角洲特种部队”。这样,一到周末这些 “网吧”的机位总是十分紧张,甚至需要预约。后来出来了,又是全国山河一片“联”,大家都通宵钻研秃鹫车战法和叉子兵rush.
后来网吧兴起,大家都咸于冲浪,鉴于上通宵总比按小时计费要便宜,自诩有着国防身体的大学生们自然比较倾向于打通宵,这不仅由于经济原因,还有着之前从电脑游戏室时代延续下来的身体惯性和风俗习惯。通宵很少见到中学生,因为他们还要上学,不到周末是断然不肯结伙跑到网吧里来打通宵游戏的,到现在也一样。
当时大学周围的大学里头的网吧里,90%以上的都是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偶尔会有一些社会青年 ,但是他们在那时犹如坐图书馆一般的上网氛围必定不会感到自在(当时大学里的网吧大多氛围都较好,大概学生把上自习和泡图书馆的习惯带了进来罢),于是又匆匆地走掉了。1999年11月和12月,我和两个朋友在川大西校区一个叫科教网吧 的地方上网,作息时间是这样:19晚上时起床,互相打传呼聚众吃饭,吃完后去网吧坐下,一直坐到次日早上八九点,然后一起去川大红河谷吃包子,吃完去街机厅耍KOF,花两块钱买七八个币,耍到11时各自回寝室睡觉,睡到19时又起来……这种作息时间保证了我们具有连续通宵的人能力,据其中一个朋友所述,之前的10月他就玩了30个通宵。其间我们经常能在网吧里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所谓“熟”就是白天在街机厅里也经常看得到的。那时我的身体还很健壮,冬天里能在连续两个通宵之后(中间不睡觉)淋个冷水澡去跑3000米,后来因为通宵太多身体每况愈下,真是恼火得很,所以没事不要瞎通宵。有一回就在网吧里,我们看见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在网吧门口打着电话,忽然就靠着门板向后滑倒,脸色铁青。知道的人说这个通宵太多,连续玩了15天,中间几乎没怎么睡觉,才搞成这个样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板们纷纷开动脑筋,有的在网吧里安放可折叠的长沙发,一些行军床则折叠起来放在门背后,另处一些地方大的网吧干脆拿出一间屋子来让大家睡觉。我见过的最大的睡觉间有4张双层床,理论上可以容纳8个人,实际不可以容纳12个人睡觉-他们让两个人挤一张下铺。临到毕业时,有一个叫李强的生工系同级熟人经常睡在一个网吧的双层床上回寝室睡觉,毕业后我又去过一个那个网吧,李强已经做了该网吧网管,每个月支300元的薪水。2000年初我常去川大外磨子桥路口的一个二楼网吧,在那看见几个似乎在玩UO的小伙子,看上去跟老板颇熟,而且好像就住在网吧里,因为无论何时我去那个网吧,总能看到他们各据一台电脑在PK或者被PK。2002年春节我又去了那间网吧,令我完全说不去话来的是那几个家伙还呆在那里,他们 看上去是那个网吧除我以外有且仅有的顾客,他们还在玩那个游戏。从口音判断,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不是成都人。然而他们 看上去已经在网吧定居,并溶入了老板一家去了--他们跟老板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一起吃午饭,沙发完全摊开,上面几条凌乱的被子……这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
通宵时也在网吧看到发羊癲疯的。2001年暑假我在成都一环路上的一个网吧里通宵,一个电子科大的学生1时走进网吧来想要打发时间。他看见我在玩“星际”,就建议单挑两三局以消磨时间。我还在攒兵,他的手突然伸过来打翻我的键盘,然后蜷缩着滑倒在地上,吐白沫,抽搐,眼角上沾着不知哪来的泥土。120急救车到了之后,他也醒了,拒绝去医院,要记录学校姓名,也拒绝了,问是否初发,回答以前没有过,然后很快走掉了。我估计他是害怕学校知道他有病。之后我再也没有在网吧里看见发羊癲疯的,那种奇观我确实还想再看一次。
在北京,靠近大学的网吧,通宵的都是一些不打游戏手就痒的大学生。离学校越远,网吧里的成分就越复杂。很多个深夜你可以看见一些使用劣质化妆品的、二十来岁的妙龄女郎在网吧里进进出出,当然会明白是怎么回事;有时她们深夜来到网吧,说明她们才起订,或者刚做完一笔买卖,有时她们深夜离开网吧,说明她们接到了单子,或者要回家睡觉。网络只是一种便宜的通讯工具。有时候可以看见一些操着外地口音的年轻人,他们多半是附近商场或餐馆的保安或服务员,但有些时候一些外地人完全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上周末在劲松东口的一个网吧里,我听到一些人在讲我们那里小地方的方言,但是我看不来他们是干什么的,只看出他们都比我年轻,在玩着某种很弱智的网络游戏。在这个网吧里我还看到一支队伍,他们的口音五湖四海,还有一个女的,他们在WOW的同一个服务器里组队做任务。天快亮时,一个北京人问:“下周什么时候?周五还是周六?”这些人周五周六地商量了一阵,终于定了时间,就各自回家了。就我推测,这些人只有周末有时间,可见是上班族,大概是一些网友不堪忍受家中慢得要死的网速或老掉牙的机器,于是来网吧通宵组队做任务。
历年所见,在网吧通宵总是男多女少,学生多其他少,大人多小孩少,青年多老头少,弱男(至少看起来弱)多壮男少,没女人的多有女人的少……其实诸多长年累月在网吧通宵玩游戏的男性青年通常都其貌不扬,肢体健壮,精力充沛,缺少异性伴侣,是游戏和网络将他们过剩的精力引导到了对现实世界不存在的事物的意淫上。
网吧与禁令
2002年6月,因为"蓝极速事件",国家曾经一度责令全国网吧禁止通宵营业并整改,那时在成都,大型网吧的通宵都停掉了,他们只从8时开到次日0时,只有一些小网吧还在自强不息地办着通宵.那些通宵的网吧,0时以后外面的大门总是关得严丝合缝,不透一点光线的,若是想进去,得先在门外面对一阵山歌,里头的人恨不得让你报上"义字当头","刀下能生","人生漫长艺术短暂"一类的江湖切口,然后铝门或铁门啪咔打开了一线,等里头的人看清你的面貌,才会让出一个人宽度来放你进去,进去之后,那门就像受惊的贝类,迅速有力地再次合上.
一起通宵的人和网吧老板私下里聊天的时候,也表现出对通宵禁令不久就会放开的信心,认为即使禁令不解除,网吧想要做生意,也总能找到办法,越小的网吧越好想办法。实际上,下达这个禁令的人不会想到,因为惧怕检查,一旦失火,这些小网吧紧闭的铝门或铁门或什么什么门,也将像蓝极速的卷帘门一样,阻挡逃生者的去路。
后来在7月,川大南门外的一家大型网吧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新开始通宵营业,真是坑灰未冷西川乱。开始他们还羞答答地营业一天关一天,说是要应付检查。但是看检查的不来,就索性直接搞通宵。后来风声似乎又紧过一阵子,但通宵终于没有停。
全国每年吸烟致死的人数有120万,相当于48 000个蓝极速,而歌舞厅这种娱乐场所也会失火,死的人比蓝极速只多不少--2000年12月25日,洛阳东都歌舞厅大火死309人,相当于12个蓝极速还多9个人;每年的矿难,死亡人数总有隐瞒,光是2004年一个河南大平矿难,就死了148人。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找出更多。
但是这些行业,都不会出现类似网吧业这样的情形(即使是暂时的)。如果消费档次比网吧高,缴纳的利税也就更多。国家也从来不禁烟,不禁采矿,每年死掉恁多人,烟照卖,矿照采。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烟草业和采矿业每年带给国家巨额的税收,如果网吧业也能带来这么多的税收,那么景遇也会改变很多吧。
初到北京的时候,因为似乎听到检查的风声,网吧们停过一阵子的通宵。但在北五环以外的地方,那些破网吧的“通宵嘉年华”依旧在随着排气扇叶子快乐地旋转起舞,彻夜不眠。到如今终于都松懈了下来,还有几个人记得蓝极速呢,而风头也就过去了。
网吧与“入室盗窃犯罪以及暴力”
中国城市的街道上经常会悬挂一些莫名其妙的标语,比如“严厉打击入室盗窃犯罪分子”。网吧左右也算“室”,所以这标语也适用于那些在网吧偷东西的家伙,应严厉打击之。
在网吧你可以经常看见诸如“提示:请看管好随身物品”的条幅,有的网吧还会在后面加上“……本网吧概不负责”以推卸责任,可以推而知之贼人之猖獗。实际上,我在网吧里从未丢过东西。多年以前,去网吧的时候什么也不带,所以也没什么好丢的;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成天背个包走街串巷,去网吧也带着。当我撇下它去上厕所,或者靠着椅子呼呼大睡进,它从未不见过,被人翻过甚至挪动过。一般来说,在一个有网管随时巡视的网吧里,想丢点东西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职业窃贼不怎么光顾这样的网吧;而你的邻座多半又全身心沉浸在游戏或Internet的世界里,眼里只有显示器没有其它。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2004年夏天我在瑞得在线网上游3楼“刷夜”,有一回在前半夜就睡着了,随即马上惊醒了---一个人正背着光站在我旁边,他看见我 ,就说了几句什么。我听不懂,问他说什么,他又说了几句什么就转身下楼了,这时我看清是一个大约十三四岁,高鼻深目黄卷发的新疆小孩,摸了全身,没丢东西。我问旁边的一个大学生这人是怎么进来的,大学生玩着游戏答非所问地笑着回答,他大概在说什么“找错人”了吧。大约是1时左右的事,这个时候网上游1楼门口刚好没人守着,可见该新疆少年早已不是生客,但与这位新疆少年的缘份,也就一面而已,之前和之后都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
如前所述,很多时候一些风俗业从业者把网络作为一种廉价的通讯手段,但是鉴于他们并不在网吧里高,显然不能算进去。不会有人在网吧里吸毒贩毒,因为网络游戏本就是“电子viper”,这些中毒者已经没有余力去吸第二种viper;也不会有人在网吧里砍人,他们都在网络里砍。一般来说更为常见的一种算不上犯罪但也不是什么好人好事的是网吧暴力,也就是在网里打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网吧里打人或者衩打的几率不会太小,相信读者诸君中心有人亲身体验过。一般来说挨打的原因不外乎作弊,在网络游戏里PK人家外带嘴欠,CS玩得太好外带嘴欠等几个原因。
规模较大的暴力行为,根据武汉某网吧资深网管车冬明所述,是当时武汉一伙玩家,挨家挨户地搜索网吧,看见在里玩道士的不由分说就拖出来打一顿。这些人多半玩战士,对玩道士的玩家保怨已久。当我还在成都的时候,在网吧里被打过,也打过人,在民风温柔敦厚的西川尚且如此,后来流窜到北方,知道北地民风剽悍,一直老老实实上网,战战兢兢做人,还没有被真人PK过,但亲眼所见和听说的网吧真人PK就不下十几起。有一起是朋友所述平日大家熟识的一个胖子,诨号“前田”的,因为CS打得好,在网吧被一伙人怀疑作弊,后来仔细看了,不是作弊,这伙人仍然截住前田,撸走了手表;另一起是同伙的两个人,因为CS进配合不好,互相埋怨,最后发展成用椅子互相真人PK。
最后,就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游戏玩得好嘴又欠,最好还是在家上网,到时就算有人想打你,也得找着人,下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网吧与网吧
如莱布尼茨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完全一样的,网吧和网吧也不一样。有大网吧和小网吧,有明网吧和暗网吧,有学校旁边的网吧和离学校很远的网吧。有电话拨号的网吧和专线接入的网吧……基本上,只要是个网吧,它就和其它网吧不大一样。
早先的网吧,多数是用电话拨号上网。据我以前一个广西朋友所述,他回广西柳城家乡,想找个网吧上网,走进去一看,56K小猫吱吱地拖着7台电脑,6个人正埋头于文字MUD,于是坐下来打开IE输入网址敲回车,6个人猛地回头怒目而视,好像在说“狗日的!又在开网页!”这时网页也都打开了,里头的图片尽是些红叉,原来网速太慢,图片都打不开……又据我以前朋友青×所述,当时川大外头太平路上的“网络咖啡”(其实是两个老板两间屋,外边coffee里面网络,两家互不相干)也是电话拨号一只小猫拖4台电脑,浏览器的缺省设置是不显示图片,而且还要9块钱一小时,当时我也曾打外头经过,依稀记得玻璃窗上的字样似乎是“通宵30元”就没敢进去坐。这都是97年或是98年的事了。
后来,成都的宽带渐渐发展起来了。先是ISDN,128K带宽。在1999年的9月,一条ISDN拖上十五六台电脑依旧慢得伤心,而且还经常断,且不说还有我这样的坏蛋常常背着老板用网络蚂蚁下载摇滚MP3听,这时往往会有在聊天室里跟MM聊得郎情妾意却被网速卡得五内俱焚的男同学跳出来大吼“哪个×人在开蚂蚁?”我就把蚂蚁暂停一下,等他坐回去几分钟,又继续下载……很快11、12月份一些新开的网吧装上了ADSL,这种情况就消失了。当时常常在通宵时先花半个小时下载四五百兆的MP3然后打开Winamp,开始一宿舒服的音乐旅程。
当初去的第一个网吧设在川大西区校医院的一楼,是很安静的所在,每小时3块,通宵12元。当时成都网吧多半是这样:设在一些民居的一楼,如果在街上,则上沿街的一个铺面,一般只有一间屋子十多台机器。最初是下机再结帐,但这样逃单的很多,后来便开始收押金了。我们在科教网吧享受2M带宽ADSL的时候,还是1999年末,当时一个上海网友问这里收多少钱,答10元,于是感叹到处都忒贵,他们那边也是每小时10元,又答曰通宵10元,网友就说大哥你哪个区我马上打车过来,再答曰在成都,那边半晌不做声。到2002年,在成都似乎就看不到在用ISDN的网吧了。天府热线的网吧我没有去过,据说华丽而昂贵。这个时候,感觉成都几乎遍地是网吧,大的小的明的暗的,于是就开始降价,每小时从3块降到两块,再5毛5毛的降,降到某些时段一块钱2小时,降到每天有2~4小时的免费时段……通宵价格也在降,从1999年的12元(还记得我在网络咖啡外头看到“通宵30元”的字样么?)降到10元(这个价格曾稳定了好长一段时间),再降到8元,然后降到6元呀5元,我上过最便宜的通宵是3元,当时半夜摸出去吃碗鸡蛋面也要3元。
2001年夏秋曾经跑过一趟北京,感觉首都就是首都,连网吧都比成都大一点、贵一截,还要登记身份证。当然我说的是那种开在居民小区外头、郭林对面、老家肉饼旁边的规模大些的网吧,五道口的什么“北京技术大学”外边的那种野鸡网吧还是不需要身份证的,但野鸡网吧不提供开水泡面,我们通宵战CS的人只好半夜去对面小卖部买汉堡吃。
接着又去了武汉,协和医科大学外面的大型网吧也要登记身份证,真是全国山河一边“登”。当时需要登记身份证的网吧多半是这个样子:进去首先要经过一个柜台,在那登记并交押金——现在柜台里头几乎都装了隐蔽的摄像头,就正对着你的脸,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然后是一个大间或者几个大间,有时楼上也别有洞天,电脑和桌凳相背着或者相向或者并排或者沿墙壁或者成列成排地整齐列着,这一格局到今天 在很多网吧里也没有多大变化;为了体现安乐祥和的气氛,很多网吧还要放一些音乐,这些歌一般都随网管喜好。当初在北京和武汉他们反复入张学友的Corazon De Melao和周杰伦的《简单爱》,听上去还可以,去年在魏公村的一个网吧,那网管放的歌可真让人酸死了,先是整夜反复入一个什么“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小薇”,后来又开始放《两只蝴蝶》《你好周杰伦》这些歌,因为那里的网管老放这种音乐,我就挪到双安商场附近的一个网吧去上网了。
从武汉回来后我去了重庆,重庆的网吧不要身份证,收费跟成都差不多;过半年回到成都,成都网吧依然不要身份证,真是好山好水好风光。这个时候,蓝极速事发,上头要整风,大网吧目标大,都停了通宵,但川大南站外沿街还有很多十几台20台规模的小网吧偷偷开通宵。我总在一个拐角处的小网吧玩通宵,不仅因为它的显示器比较好,这个网吧总在半夜1时人最饿的时候向客人提供一纸饭盒的热粥,里头掺有炒玉米和小块的泡菜,味道十分好,吃了后半夜很精神。以后我再没遇到过这样充满着终极关怀和人本主义的网吧。当时(2002年夏)的价格是每小时元,通宵6元。现在成都什么样子我不太清楚,每个小时两块钱好像已经多年没有变过,但在北京是不一样的,可以说,首都人民的消费跟首都的政治地位一样高。2004年3月有一阵我居无定所,天天跑魏公村的瑞得在线网上游上网兼睡觉,通宵20,饶是如此,旁边民族大学的学子们还是踊跃报名。春天到了价钱就降了,降到15元。但是网管放垃圾音乐,只好跑去双安旁边的地下室,瑞得在线泰丰宇,一宿收12,这价钱才有点人样。但我依旧要说,12块钱我两年前在成都都要耍两个通宵,而且还有热粥喝,这就是国际大都市的消费水平吗?
泰丰宇的厕所蹲位都拿板子隔开,板子离地大约有30厘米。一回我从厕所出来,遇着一个男的和一个姑娘往里钻,余光瞅着那姑娘也跟着进了男厕所……20000年的成都的一个网吧搞过什么情侣座,一人多高的隔板把两个座隔在里面,四面围住院了三面还多,人一坐进去外面就看不见了,也不开大灯,这种座们我坐进去键盘都看不大清楚,只要你不搞得太响,没人会知道你在做什么。不久之后就被勒令整改,搞了现在那种无隔板的电脑桌,大厅灯一开,一览无遗。
哪也比不上家好
1999年上网到今,大约有2/3的网络时间是在各种网吧里度过的。就我的看法,如果家里安装了宽带,自然是在家里上网最好,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你就是嘴欠一点人家多半也拿你没什么办法。而网吧,一般来说,有恶劣的空气和昂贵的饮食,这且不说,重要的是,这网吧,它不是你的家。
阅读 5569
全部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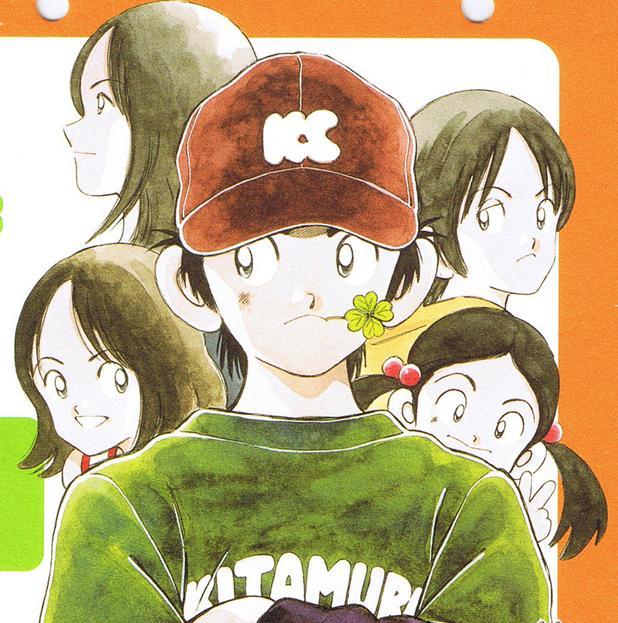
我爱王江漫
· 云南没在成都住有年头了...
亮了(0)
回复

阿利吉耶里
新买的鼠标好滚轮!!!
亮了(0)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