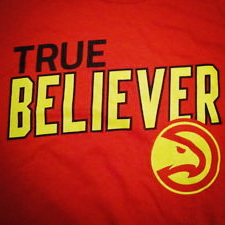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打开APP
拙劣到惊人的译作——论《梦之队》于嘉译本
一本无稽的译作,一串无奈的问题,一场注定无用的批评
。
“with a bow tie, a lit cigar, and a dictator’s fist”
原文:It was not the result of a crusade by the NBA’s marketing demons to sell $200 Authentics in Europe, even though that was an eventuality.
在我看来,译者完全就是跳过了“crusade”(十字军远征)、“demon”(魔鬼)、“Authentics”(指AU球衣,又称球员版球衣/多层电绣球员版球衣,是NBA正品球衣中价格最高的)这些(超过高中水平的)单词,光盯着“NBA”“marketing”“sell”,生生创造出了“NBA一次可以载入教科书的经典市场推广案例”的译文。
至此,我已经很难区分译者到底是在翻译还是在二次创作了。而这种肆意创作,常常伤害了原文的韵味。比如这句:
我想,大部分读者跟我一样,不知道这句话在说什么。实际上,原文讲的是美国青少年中流行的一种游戏,大家围成一圈,其中一个人转瓶子,瓶口指向谁,谁就要跟转瓶子的人亲嘴。大卫•罗宾逊会收到白人孩子的邀请,去参加派对,但在转瓶子这个游戏环节,白人孩子们却会很自然的说:你来当裁判。
“这是打着我的名字出版的第五本书……第二本是翻译的……第四本是翻译作品……到了这一本,就算是我出书的巅峰了……这本书是我出的书里的巅峰。不为别的,因为我爱篮球;而书里的所有人和事,就是我爱上篮球的原因。”
我先不吐槽这位译者出于对篮球的爱而出版的巅峰之作就是这么个玩意儿这回事儿了。我更惊讶的是,为什么能有这位译者有这么好的资源,会有三本书稿找上他来翻译?
。
——题记
大约两年前,我买了一本英文版的《Dream Team》。 这本书的作者是Jack McCallum,《体育画报》——美国最重要的体育杂志——篮球专栏首席写手。梦之队是1992年的事情了,McCallum在20年后重新回顾了那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队,还给出了很多内幕消息和独特看法。除了内容吸引人外,McCallum的语言也非常之棒。有的章节,我读完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跟其他篮球爱好者分享,还在虎扑上翻译了其中一章。
大约一年前,我又买了译文版的《梦之队》。
因为事情太多,之前那本英文版的书,后半本没有读完。所以在网上看到中译本的时候,我非常高兴,马上买了一本。读中文还是比英文畅快得多——尤其是对于我这样喜欢一边读一边翻译的人来说——大概一两天的时间,就很顺畅地看完了整本书。
但很让我在意的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察觉到了两个低级错误。
大约一年前,我又买了译文版的《梦之队》。
因为事情太多,之前那本英文版的书,后半本没有读完。所以在网上看到中译本的时候,我非常高兴,马上买了一本。读中文还是比英文畅快得多——尤其是对于我这样喜欢一边读一边翻译的人来说——大概一两天的时间,就很顺畅地看完了整本书。
但很让我在意的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察觉到了两个低级错误。
63页:“……罗宾逊加盟了海军学院。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校园里……”
美国海军学院位于安纳波利斯(Annapolis),而非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
美国海军学院位于安纳波利斯(Annapolis),而非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
290页:“在第二战之前的夜里,乔丹飞到了亚特兰大的赌场,豪赌了一个通宵。”
美国对开设赌场有严格的限制,绝大多数城市都不能开设赌场。乔丹飞去豪赌的一定是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而非亚特兰大(Atlanta)。
这让我产生了两点想法:
美国对开设赌场有严格的限制,绝大多数城市都不能开设赌场。乔丹飞去豪赌的一定是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而非亚特兰大(Atlanta)。
这让我产生了两点想法:
(1)这译者有一种“我不认识的城市都不存在”的自信,只有拥有NBA球队的城市才有资格在他的书里存在。
(2)这译者的用心程度还比不上那些用谷歌翻译来糊弄差事的家伙,哪怕是在百度里搜一下“Atlantic City”,也不会搞错成“亚特兰大”呀。
之前说过,我有边读书边翻译的习惯。于是翻出了自己过去的译稿,比对了一下。
结果令人震惊。仅仅第一章,按我的译文是3206字,就出现了大大小小22个错误。
下面摘取几条。
原文:...he had come on behalf of FIBA.
译文:过去的一半岁月里,他都在FIBA供职。
错误:认错单词,将behalf(代表)误认为half(一半)。
之前说过,我有边读书边翻译的习惯。于是翻出了自己过去的译稿,比对了一下。
结果令人震惊。仅仅第一章,按我的译文是3206字,就出现了大大小小22个错误。
下面摘取几条。
原文:...he had come on behalf of FIBA.
译文:过去的一半岁月里,他都在FIBA供职。
错误:认错单词,将behalf(代表)误认为half(一半)。
参考译文:他这次是代表FIBA前来。
原文:In the Balkan area of Yugoslavia... the people measure eras not by “war and peace” but by “war and non-war.”
原文:In the Balkan area of Yugoslavia... the people measure eras not by “war and peace” but by “war and non-war.”
译文:(巴尔干地区)在这里,人们耳边最常听到的,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战或不战”。
错误:认错单词,将era(时代)误认为ear(耳朵)。
参考译文:在巴尔干地区,人们区分各个时期时,用的不是“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而是“战争年代和停战年代”。
原文:And for the next decade and a half, no one except Boris Stankovic went there.
原文:And for the next decade and a half, no one except Boris Stankovic went there.
译文:随后十多年里,斯坦科维奇再没去过美国,因为没有人希望他再去那里。
错误:认错单词,将except(除了)误认为expect(期待)。
参考译文:接下去整整一十五年里,没有人再去过美国,除了鲍里斯•斯坦科维奇。
原文:...Robinson hit the social glass ceiling in his high school years.
原文:...Robinson hit the social glass ceiling in his high school years.
译文:在高中的时候,罗宾逊的社会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错误:认错单词,将glass(玻璃)误认为class(课)。
参考译文:高中时代的罗宾逊撞上了社会的玻璃天花板。
除了这些中考英语不及格水平的错误,译文中还有大片大片的漏译,比如第一章中的下列句子,在译文中完全不见踪影。
除了这些中考英语不及格水平的错误,译文中还有大片大片的漏译,比如第一章中的下列句子,在译文中完全不见踪影。
“with a bow tie, a lit cigar, and a dictator’s fist”
“The type of meat Stankovic most liked to inspect, though, was the cured leather on a basketball”
“He was just an outsider trying to learn the nuances of American basketball while also trying to learn how to order a hamburger”
“given the sicio-political sports climate”
“a loathsome individual, a clear number one on the list of tin-pot despots who have run sports over the centuries”
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原文:It was not the result of a crusade by the NBA’s marketing demons to sell $200 Authentics in Europe, even though that was an eventuality.
译文:这也不是NBA一次可以载入教科书的经典市场推广案例,尽管它最终产生了这样的作用。
参考译文:不是NBA营销部的恶魔们为了发动将AU球衣200美元一件卖到欧洲去的远征——虽说这件事情后来确实成真了——而造成的结果。
在我看来,译者完全就是跳过了“crusade”(十字军远征)、“demon”(魔鬼)、“Authentics”(指AU球衣,又称球员版球衣/多层电绣球员版球衣,是NBA正品球衣中价格最高的)这些(超过高中水平的)单词,光盯着“NBA”“marketing”“sell”,生生创造出了“NBA一次可以载入教科书的经典市场推广案例”的译文。
至此,我已经很难区分译者到底是在翻译还是在二次创作了。而这种肆意创作,常常伤害了原文的韵味。比如这句:
有一次他去参加派对,当天花板上的七彩激光球开始旋转时,有人对他说:“好了,大卫,你现在可以当裁判了。”
我想,大部分读者跟我一样,不知道这句话在说什么。实际上,原文讲的是美国青少年中流行的一种游戏,大家围成一圈,其中一个人转瓶子,瓶口指向谁,谁就要跟转瓶子的人亲嘴。大卫•罗宾逊会收到白人孩子的邀请,去参加派对,但在转瓶子这个游戏环节,白人孩子们却会很自然的说:你来当裁判。
通过这个小小的情节,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大卫•罗宾逊的成长历程和性格形成。
至于译文中的“天花板上的七彩激光球”……真不知道是哪儿冒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译者的翻译套路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译者的翻译套路是这样的:
遇到没听过的城市名,就翻译成另一座以前听过的城市;
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当成另一个拼写差不多的单词接着翻译;
遇到没听过的事情,就找一出以前听过的事儿给安上;
遇到读不懂的句子,就……这回倒是没换,直接就给删掉了。
然而,更神奇的地方在于,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我读到了作者的后记:
然而,更神奇的地方在于,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我读到了作者的后记:
“这是打着我的名字出版的第五本书……第二本是翻译的……第四本是翻译作品……到了这一本,就算是我出书的巅峰了……这本书是我出的书里的巅峰。不为别的,因为我爱篮球;而书里的所有人和事,就是我爱上篮球的原因。”
我先不吐槽这位译者出于对篮球的爱而出版的巅峰之作就是这么个玩意儿这回事儿了。我更惊讶的是,为什么能有这位译者有这么好的资源,会有三本书稿找上他来翻译?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本书中,有整整12页的推荐序,分别来自赖声川、张卫平、徐济成、姚明和张佳玮。这些人的名字和推荐语也同样印在封底上。
为什么一个连glass和class、era和ear都分不清的人,能接二连三地得到翻译出版的机会,还能请到那么多大咖前来推荐?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护封勒口的译者简介上。
不是“于嘉”这两个字,而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CCTV5)著名主持人”。
挑几个错,挂出来,不是难事,也算不上本事。
我写东西,总还是希望,能提出几个问题,给出一些答案,给读者以启发,给爱好篮球的朋友们一个深入思考的契机。
在这里,我想简单就篮球领域谈一谈:我们为什么会拿到这样一本糟糕的译作?我们该拿这样一本糟糕的译作怎么办?
一本糟糕的译作,责任编辑有责任,国内出版环境有责任,国内翻译环境也有责任,但究其根本,最大的责任还是在译者身上。
挑几个错,挂出来,不是难事,也算不上本事。
我写东西,总还是希望,能提出几个问题,给出一些答案,给读者以启发,给爱好篮球的朋友们一个深入思考的契机。
在这里,我想简单就篮球领域谈一谈:我们为什么会拿到这样一本糟糕的译作?我们该拿这样一本糟糕的译作怎么办?
一本糟糕的译作,责任编辑有责任,国内出版环境有责任,国内翻译环境也有责任,但究其根本,最大的责任还是在译者身上。
我认为,于嘉先生在主观上确实是认真对待这份稿子的——如果他只是想着交差了事,干脆“谷歌翻译”一下,正确率也会比现在高——这恰恰说明了他的亲力亲为。
然而认真对待却只翻译出了这么个玩意儿,只能说明……
然而认真对待却只翻译出了这么个玩意儿,只能说明……
第一,于嘉先生的英文水平实在不过关。
第二,于嘉先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首先要归咎于惩罚机制的缺失。
这首先要归咎于惩罚机制的缺失。
根据出版总局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质量包括内容、编校、设计、印刷四项。内容质量只关乎内容是否危害国家统一、国土完整等。编校质量,也只有“知识性、逻辑性差错”这一项擦到边,但处罚的对象是编辑和出版社。因此,在现行图书质量管理体系内,译者胡乱翻译一气并不会得到任何处罚。
不要说“处罚”,哪怕让步到“道歉”的程度,恐怕也是奢望。中国的篮球媒体从业人员在专业方面犯的错误,已经多到不足为奇的地步。不久前,就在两三天时间里,前有评论员不识单词、乱翻译新闻、引导舆论,后有外派记者在采访中现场编造球员言论。这些事情还是因为发生在名人身上或关键战中才被抓住的。更不用说不知名比赛中不知名媒体人员的错误。但有哪一次,我们得到过一个干净利落的道歉?
其次是流动机制的缺失。
其次是流动机制的缺失。
篮球界有句名言——“你行你上啊”。这句话其实预设了一个有着丰富流动机制的环境:如果你的能力更强,环境就会欢迎你来取代专业能力不如你的前任。篮球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流动性极强的环境,板凳末段的球员抓住机会就能进轮换甚至首发。
与之相反的是,国内的篮球媒体流动性却非常低。体制内自不用说,因为“编制”的存在,流动性更低,得等到孙正平退休,才有机会空出缺来,补上黄子忠。体制外也差不多。这些年,从新浪到腾讯,无论解说还是嘉宾,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人,而且无论犯下什么错误,除非违法乱纪引来政法机关,否则都还是端坐不动,不会被他人取代。
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力”的重要性降低了,让位给了“关系”。
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力”的重要性降低了,让位给了“关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人见到glass和class不分的于嘉先生,都要称一声“老师”,还有那么多人为这本糟糕的译作写序。央视至今仍然是曝光度最高的媒体,维持与央视的关系自然是最重要的事情。
讽刺的是,身在其中的人物自己倒看不清,常把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混为一谈。所以每每在被指出错误时,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而是对对方的鄙夷,而且是对地位的鄙夷,字里行间透出来的都是“你算老几”。
另一方面,这种环境还造成了专门化程度低、分工不清的情况。
讽刺的是,身在其中的人物自己倒看不清,常把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混为一谈。所以每每在被指出错误时,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而是对对方的鄙夷,而且是对地位的鄙夷,字里行间透出来的都是“你算老几”。
另一方面,这种环境还造成了专门化程度低、分工不清的情况。
以美国的NBA媒体为例,有专门负责讲解场上情况的解说,有跟球员打交道、呈现球员剪影的杂志记者,有爆料、抢发新闻的新闻记者,有对战术、数据等进行评价和分析的专栏写手。互相之间偶尔也干点别人的活计,但主要还是做自己专门的事情。
反观国内的篮球媒体,直到今天,解说和嘉宾之间的分工都还没搞清楚。每个人都试图做全才,既做实况解说,也写球评分析,还兼着卖衣服的副业,来个翻译的活儿也不推辞。
反观国内的篮球媒体,直到今天,解说和嘉宾之间的分工都还没搞清楚。每个人都试图做全才,既做实况解说,也写球评分析,还兼着卖衣服的副业,来个翻译的活儿也不推辞。
国内的图书市场本就不大,再细分到体育领域下的篮球领域下的译作,数量就更少。在这么狭窄的市场里,那些真正通晓篮球、认真翻译、用心对待作品的人,却得不到多少机会。出版社寻找译者,不知道如何分辨能力,只知道循“头衔”寻之。因而,专门化程度不高的人却能屡屡跨界为之,如此一来,我们得到这样一本糟糕的译作,也是正常的事了。
这篇文章,是我写过的,最让自己郁结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我写过的,最让自己郁结的文章。
文章的前半段,也就是挑错的部分,我很早就完成了。后半段,竟写了将近一年。一是因为这其中的弊病太多,千头万绪,互为表里,想找出造成此种现象的关键源头,却实在很难理清。二是因为就算理清了,也没有用——本文的主题,不就是在分析为什么这篇文章一定没有个结果吗?
想来想去,还是要把这篇文章写完。尽管没有用,发出呐喊声总是好的。呐喊替代不了火光,无法照亮黑暗。但把沉静在黑暗里的人们叫醒,才有机会,想出点亮火光的办法。
发布于浙江阅读 102306
这些回复亮了

ItTakes5
· 黑龙江这个翻译.......简直就是负分 这种书出版都不需要校对嘛
亮了(1235)
查看回复(2)
回复

丸户惠
· 河南讲道理安纳波利斯和大西洋城这两个,可以理解为对美国不熟悉,勉强可以接受 但楼主之后提出的那几个,behalf,era,except,glass都译错,这就纯粹是水平问题了
亮了(888)
查看回复(7)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