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打开APP
简单影评杨德昌电影《一一》
影片《一一》首映于2000年,是台湾大师杨德昌的最后一部电影。《一一》无疑是杨德昌最为成熟的作品,也是其最被大众所接受的作品。此片不同以往那样的冷漠、凌冽,多了许多温情、柔和。杨德昌的导演技法也是相当圆润,即使此片同《海滩的一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样,时长相当长,内容元素也足够多,但技法成熟得像是能磨平各种元素棱角的刀,将其有序而又有趣地摆放在173分钟的时长里。影片中一些别有深意的符号、一些剪辑上的平行蒙太奇、音画蒙太奇、一些影像上利用镜子和玻璃的特殊表达、音轨被落后或提前于画面的转场,将一个塞满了性启蒙、家庭婚姻危机、宗教信仰感叹、社会时政的讽刺、日 美 大陆与台湾复杂关系的故事裁剪整齐而又恰当。文本上扎实的剧作结构、几线故事平稳的叙事功力、台词对白上饶有深意的设计。这一切都让其成为了一部伟大的作品。
杨德昌在《一一》中还是延续了自己电影生涯的永恒母题——都市空间与时代转型对人的异化和改变。虽整部影片的大基调同过往作品一样客观、冷静,但相比较于《海滩的一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青梅竹马》、《恐怖分子》而言,杨德昌少了很多冷漠与凌冽,多了一丝温情。
《一一》在接近三个小时的时长里装载了太多元素和内容,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几处精妙技法——音画分离、镜子道具、影像暗示。
有人说《一一》像是讲清了一个人的一生,我是认同的。影片的开篇是婚礼,在温馨轻柔的钢琴曲衬托下还有几声婴儿的哭啼声,整个开篇显得明媚与阳光。这就像是人的“生”。
第一处影像暗示是在影片的第三分四十秒处。NJ在阿弟的婚礼上帮忙,忙中出错的他将阿弟与阿燕的结婚照片倒挂。
这一处影像上暗示了阿弟与阿燕的婚姻生活有着诸多问题。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们逐渐注意到阿弟和阿燕的结合、经济状况,在各方面都有着问题,但在影片一开始的婚礼上,杨德昌就通过NJ的一次“帮忙”对两人的婚姻家庭有了暗示和基调铺垫。
而直到在影片第九十九分钟,结婚照片再次出现。这一次结婚照片稳稳当当地挂在墙面上——象征这两个人的婚姻家庭问题得到解决,两人关系和家庭也逐步稳定。剧作也以阿燕救出浴室中瓦斯中毒昏迷的阿弟作为二人和解的突破口。最引人称赞的地方在于,杨德昌在这里使用了一个长镜头。阿燕从房门进来,镜头直视阿燕,之后阿燕运动到客厅,镜头摇镜跟随,阿燕发现异常去浴室,但镜头没有跟随阿燕,而是继续摇镜到了结婚照片上成为固定机位,仍由浴室中阿燕的呼救声放出而镜头不动。杨德昌不用去展示阿燕救出阿弟的场面,只用将镜头给到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片即可,与开篇NJ手中的倒挂结婚照片形成影像上的呼应——自己想表达的、观众明白的都在这一对呼应当中。
《一一》探讨了许多东西,诸如性启蒙、家庭婚姻危机、宗教信仰感叹、社会时政的讽刺、日 美 大陆与台湾复杂关系。但我对性启蒙这一个话题分外感兴趣,影片在第九分五十三秒处,第一次介入了性启蒙的暗示。
杨德昌在这里使用了音画分离的技巧,用声音与画面的分离制造出了特殊的蒙太奇效果。婚礼当中,洋洋母亲与老同学们探讨先上车后补票的事情,但镜头一直对准洋洋。之后剪到几个同龄女生身上,镜头仿佛跟随这洋洋的眼神而移动到那一堆女生当中,这一个镜头充当了洋洋的视点,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个主观镜头。但在这连续的两个镜头里,声音来源都是洋洋母亲的同学在大讲男女之事。这一组巧妙的音画分离镜头成为了第一处探讨洋洋性启蒙的地方。
第二处是在影片二十分零五秒出,洋洋学校中的“小老婆”第一次出场。
这个镜头里,机位没有作出改变,但这样的构图使“小老婆”从高处走下来映入观众视线的第一处便是“腿”,这个机位也模仿了洋洋从下往上打量“小老婆”的眼神,再次充当了洋洋的视点。对“腿”的着重刻画和从下往上地打量,都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就更不用说剧作上洋洋在这里将保险套当做气球进行玩弄了。在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就对“腿”着重刻画,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也使用了很多从下往上的镜头去模仿从下往上的主观视点。
第三处是在影片第八十五分十二秒处,洋洋进入黑漆漆的会议厅参加科普讲座。“小老婆”迟到进场时,那一个镜头的刻画,已经是极其明示。
“腿”依旧成为了这里着重刻画的元素。而撩起的裙边成为了更为直接的明示。不过仅仅是这样还谈不上是惊喜,作为大师的杨德昌再次使用音画,暗示了更多东西。
“正电”、“负电”、“激烈地结合”这样的旁白伴随着雨声和雷声的音效,屏幕上不断翻卷的云和“小老婆”的背影 ,洋洋的性启蒙达到了一个高点。
影片在二十九分时,莉莉、婷婷和胖子这三人线索第一次正式相遇,开启了这个三人故事。而影片也在这三人故事的一开始对三人故事作出了暗示。
“红色信号灯”成为了影像上的暗示,已经提示三人故事的悲惨走向。
影片在八十五分五十八秒时,婷婷和胖子二人终于开始走到一起。而此处的影像更值得琢磨,它似乎解决了两个问题——婷婷和胖子的结局是何?婷婷和胖子又为何在一起?
结局是何?影像上的“红色信号灯”已经再次给出了答案。为何开始?婷婷和胖子二人的站位也给出了答案——相似的机位和景别对应了相似的境遇和内心感受 ,镜像的人物站位暗示着分道扬镳的命运结局。
影片在第一百五十三分钟处,给出了婷婷、莉莉、胖子这条三人故事的结局 。剧作上的表达是胖子用刀捅死了莉莉的英语老师——以流血事件结束故事线似乎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海滩的一日》、《青梅竹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都有着相似表达。但在影像上,杨德昌利用“红色警灯”给予了影像上的完美呼应。
音画分离是杨德昌在《一一》中的惯用技法,已经在影片九分五十三秒处对婚礼上的洋洋进行了使用。而在影片第三十九分十六秒处,再次进行了一次音画分离的使用,这一次似乎是杨德昌本人的私货。
画面上是阿弟陪阿燕去做孕检的孕检图,但音效是NJ的日本合作伙伴的PPT展示介绍。孕检图中的新生生命和PPT介绍里的电脑游戏(在2000年左右,也可以看做是新生生命)成为了既无关又相关的组合。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似乎杨德昌的认识是对的。
影片在第六十一分处,第三次作出了音画分离的效果,而这一次直接指向了杨德昌电影生涯里的永恒母题——都市空间与时代转型对人的异化和改变。
隔壁蒋家在争吵,NJ关上了自家窗户。窗户的玻璃映射出繁华的台北夜景,但音效却折射出家庭的分崩离析。城市空间和时代转型对人的异化和改变在这一刻被影像所传递。
第四处音画分离是在影片第八十一分三十三秒处,阿弟去前女友云云家借钱,之后二人同躺一张床上看电视聊天。
两人聊天的内容是阿弟借钱给朋友,但云云说他跑路了,但背景音效是电视机里的情色电影的呻吟声。这段音效暗示了云云的欲和二人旧情复燃的关系。在剧作与影像上没有对二人性有直接描述,但通过音效却暗示了云云的欲和性。剧作上在九十七分钟左右,由NJ和阿弟的谈话揭露了谜底,阿弟一直在为云云“服务”,但这种“服务”已在这里通过音效作出了暗示与铺垫。
在华语电影世界里,我一直认为王家卫对镜子道具的使用是炉火纯青而又别有意味。但在杨德昌的《一一》里,也多处使用了镜子(玻璃)道具,对影像有了更深层的塑造,对传递有了更有力的传达。
在影片第十七分四十五秒处,杨德昌第一次使用了镜子道具。
婆婆住院,NJ和阿弟都赶来医院。在医院的走廊上,阿弟对NJ再三承诺会还钱的事。为什么杨德昌在这里要作镜子道具,因为镜子里的世界是虚无的,影片直到最后阿弟也没能够还上NJ的钱,就如同这里镜子中的承诺一样,是镜中月、水中花,虽然美好,但现实还是很无奈的。
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镜子(玻璃)道具段落是影片第六十四分二十秒处。敏敏下班后一人在办公室里发呆,同事问敏敏为何不回家,敏敏回答:“我没有地方去”。
窗外是繁华的都市,窗内的敏敏却说“我没有地方去”,一丝“虽万家灯火却无一是我”的悲伤情绪涌上心头。虽这样的情绪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在这里使用镜子(玻璃)道具却能在影像上有着更强烈的冲击力,对杨德昌的永恒母题——都市空间与时代转型对人的异化和改变而有了更深的传递。
相类似的,镜子道具直指杨德昌母题的段落在本片中还有一处。在一百三十四分十五秒处,阿瑞与NJ在东京游完一天后,阿瑞回宾馆房间内哭泣的场面 。
阿瑞步入房间后开始哭泣,表层是因阿瑞故地重游而因爱情落泪,其实深层还是直指杨德昌的永恒母题——都市空间与时代转型对人的异化和改变。阿瑞在东京城市群下的孤独身影若隐若现,影像所传递的力量绝不是台词或旁白可以替代。
另外在好几个段落里,摄影机都没有穿过玻璃或镜子,而是将观众与人物隔开。更加展示了人物被囚禁,被框住,找不到生活出口的状态。比如四十八分零五秒处莉莉等待胖子的场面,比如六十七分四十六秒处NJ发现同事仍然抄袭时的无奈。
杨德昌的剪辑能力早在《海滩的一天》中有所展示,将众多子题和三重叙事玩弄得游刃有余而不累赘。在《一一》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剪辑是影片第一百零九分开始的一段蒙太奇。
杨德昌将在台北和胖子约会的婷婷和在东京同阿瑞约会的NJ进行了巧妙的剪辑,构造出了一段惊艳的蒙太奇。不仅是相似的影像和剧作,杨德昌在音效上仍然下了功夫,音轨被做了特殊处理,音效提前或落后进入了画面而成为了串联起两个时空的工具。这样的处理将台北、东京、女儿、父亲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让观众有了宿命感与轮回感,让观众看后不知不觉便有了一种《一一》是人生的感觉。而在此处,这样的处理其实也透露出了杨德昌的一些人生观。
《一一》虽然镜头沉稳,角度客观,但已不像之前作品那样冷漠、凌冽。甚至在一百五十九分处,杨德昌构造了一段超现实主义段落,这是之前他的作品里罕见的。
婷婷恍惚看见婆婆病好了,坐了起来。婷婷走过去说:“你原谅我了”。之后婷婷终于睡了一个好觉,醒之后发现婆婆离开了人世。这处超现实主义段落不仅是婷婷对自我的一次和解——在婷婷、莉莉和胖子的三人关系中终于解脱——婆婆下楼扔垃圾也是因为当初婷婷当初在阳台上偷看莉莉和胖子而忘了扔垃圾所导致,其实也是对婆婆即将离世的一次暗示。在杨德昌最后一部影片中这样温情地构造了一个超现实主义段落,可能也和当时的杨德昌能理解更多的生死有关。
最后,有两处影像上的细节我觉得很有趣。一处是一百零七分时,NJ和阿瑞在东京游完,阿瑞故地重游激起了年轻时的回忆。
要我说,这简直是对挚友侯孝贤的一次照搬 。剧作上阿瑞在谈和NJ过去的岁月,但影像上用铁轨和火车代替了流逝的时间。这里的意象几乎是侯孝贤导演生涯的永恒母题。
第二处是一百二十分十秒处,胖子和婷婷在听音乐会。
台上弹奏钢琴的是杨德昌本人,拉大提琴的是杨德昌的第二任妻子彭铠立。台下坐的是婷婷和胖子。想起杨德昌与蔡琴、彭铠立的故事,对应着台下莉莉、婷婷和胖子的故事。戏里戏外,似乎都是人生。
总的来讲,《一一》一定是一部留名华语影史的佳作。它沉稳内敛、技巧成熟,主题上包罗万象而富有人生哲学。试图剖析它永远都是一个大工程,我只是对我感兴趣的几个技巧上的点作出了梳理——音画分离、影像暗示、镜子道具。
总的来讲,《一一》一定是一部留名华语影史的佳作。它沉稳内敛、技巧成熟,主题上包罗万象而富有人生哲学。试图剖析它永远都是一个大工程,我只是对我感兴趣的几个技巧上的点作出了梳理——音画分离、影像暗示、镜子道具。
发布于四川阅读 13080
这些回复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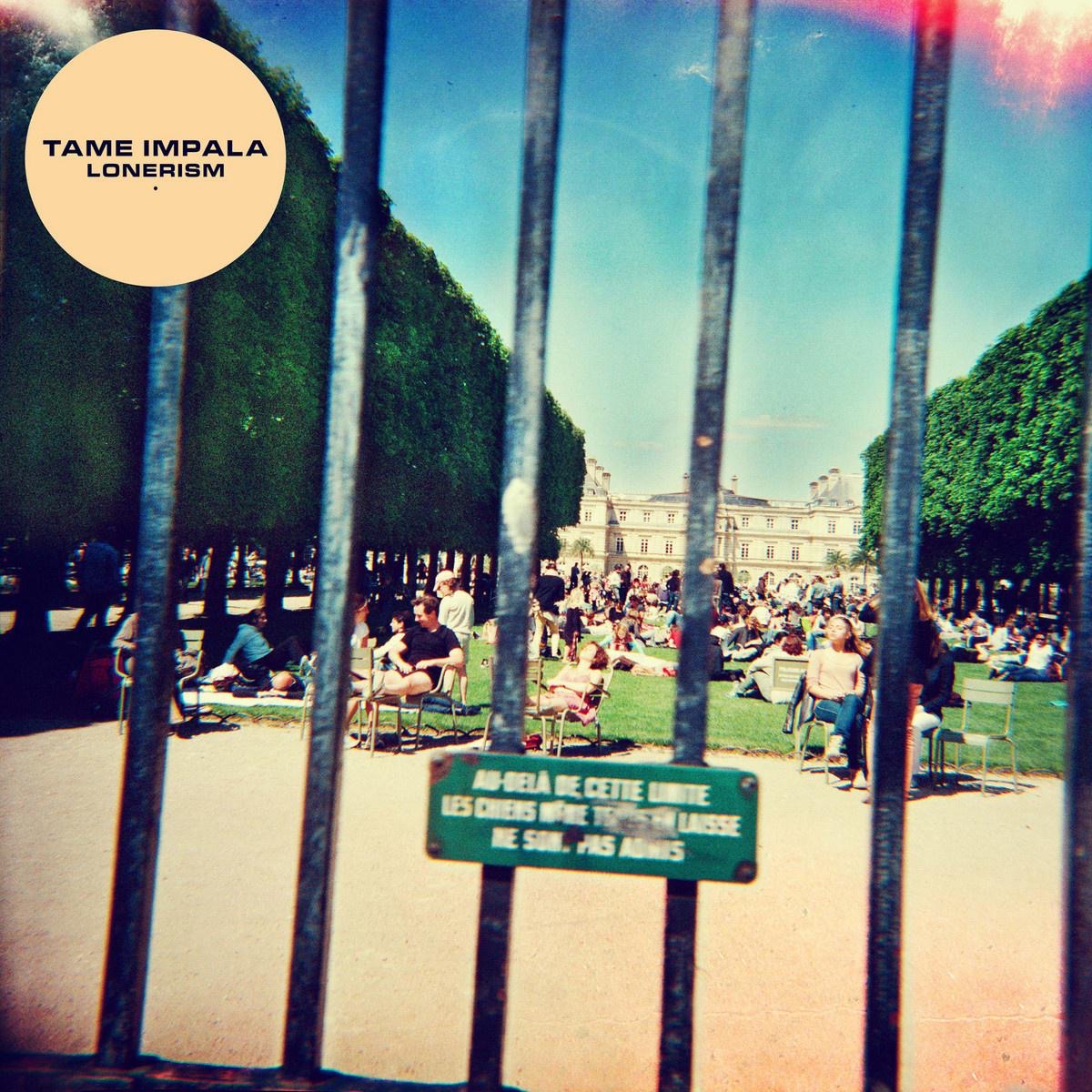
electricbblue
· 广东音画分离➕平行剪辑是杨导特别爱用的,前者在牯岭街里也特别多
亮了(19)
查看回复(1)
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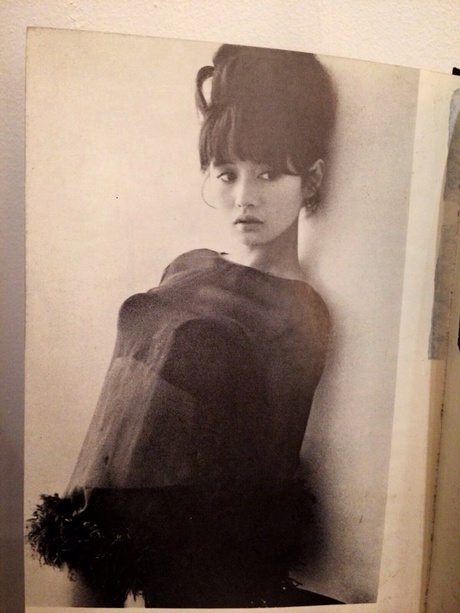
头文字L
一一最喜欢洋洋那段,拍后脑勺真的是神来之笔,以前杨德昌电影没见过的,杨德昌的电影除了牯岭街,其他所有几乎都是在探讨城市化过程当中城市中产的焦虑和困境,对大陆观众来说是相当更有共鸣的,台湾本土情结可能会相对少一点,所以台湾影评人其实是更推侯孝贤的,大陆反而欣赏杨德昌的影评人更多一些
亮了(21)
查看回复(2)
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