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南怀瑾先生:孟子起码花了二十多年的工夫,才做到不动心的境界
历史的乘除
孟子说:使一个国家称霸,使一个国君成名,又算得了什么?我认为要使齐国称王天下,就像自己把手掌翻过来一样的容易。我们现代的成语“易如反掌”,就是从孟子这句“由反手也”来的。孟子说得如此容易,我们可以说他的牛可吹大了。且看下文。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镃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
孟子说使齐国称王天下,就像自己一翻掌那么简单。公孙丑听了,对他老师的话表示怀疑,他说:照老师这么说,使齐国称王天下,像把自己手掌翻过来那么容易,这就使我愈来愈糊涂了。就以历史的事迹来说,称王天下谈何容易,像周文王这等人才,当政差不多百年,他当时那样地厉行仁政,也并没有完成一统,还是靠了他的两个儿子——武王和周公继续努力下去,然后慢慢经过了百多年才成功的。
实际上,周朝统一天下,掌握政权达七百多年之久,这样深厚的基础,并不只是周文王父子两代奠定下来的,而是由古公亶父,乃至远溯至公刘,更向上推至后稷,这样好几百年一路下来奠定的基础。犹如秦始皇的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也不只是秦始皇的功劳,而是秦国在一两百年前就开始建基的。并不像后世来自民间的帝王,例如明代朱元璋那样,原来只是一个落魄的和尚,结果在民间突然崛起,做了统治全中国的皇帝,这是特殊的现象。这也就是古今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模式。
我们再看看“治世百年,殷之顽民未化”的历史记载。周朝的政权建立了一百年以后,前朝的遗民、殷商的拥护者仍然不肯接受周朝王道德政的感化。由此可见教化社会人心的困难,这是我们读历史必须注意的一个关键。以文、武、周公之德、之才、之能,“治世百年”尚且“殷之顽民未化”,便知天下事实在不像翻一下手掌那么容易。这也就难怪公孙丑“惑滋甚”,对他老师孟子“以齐王,由反手也”的话想不通了。
所以公孙丑说:你说王天下那么容易,那么文王也不值得效法学习啰?这是公孙丑用孟子的话反过来向孟子质疑。因为孟子是最推崇文、武、周公的,所以现在公孙丑这样发问,等于说:那么老师你比文王、武王,比周公还要伟大,还要高明了?
孟子对于文、武、周公、孔子,始终尊敬如一。他说:如果以文王来比我,那又不敢当。不过我说我可以使齐国称王,是另有理由的。当年文王、武王的情形和现在不一样,首先,文王、武王当年的对象是前朝商汤。商朝由汤王传到武丁,有数百年之久,其间有过六七位圣贤之君。五六百年间出六七个圣贤的君主,这是很难得、很了不起的盛世。我们算算历史的账,在以往的历史中,以武力最强、文化又发达的汉唐两代来说,汉代在汉高祖以后,文帝、武帝、宣帝之外,没有几个好皇帝。唐代在唐太宗以后也没有几个好皇帝,唐明皇算是半个,但是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也就糊涂了。还有一个唐宣宗,他也是做过和尚的,虽然他没有真的出家,但的确也剃了头,做了一阵禅和子,与黄檗、香严禅师都是要好的同参道友。有一次他与黄檗同住在江西的百丈山上,曾因同观瀑布,和黄檗联句作诗,不过也有人说和宣宗联句的是香严禅师,并非黄檗。这首诗是这样的: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黄檗起句)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宣宗联句)
后人看了唐宣宗的末句“终归大海作波涛”,认为是唐室衰微的谶语,因为唐朝自宣宗以后即天下大乱,接近尾声。还有宣宗做和尚时,题百丈岩的一首诗也很好:
大雄真迹枕危峦 梵宇层楼耸万般曰月每从肩上过 山河长在掌中看仙峰不间三春秀 灵境何时六月寒更有上方人罕到 暮钟朝磬碧云端
这都是他少年时代为了逃避唐武宗的猜忌,剃头出家去学禅时的作品。据《林间录》记载,他全靠太监仇公武的庇护,剌头出家去参禅也是仇公武的计划。这个姓仇的太监,大有类比丙吉当年保全汉宣帝的大功。
唐宣宗说“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日月星辰都从他的肩头上运行过去,大地山河也在他的掌中一览无遗,这到底还是帝王的气魄。后世称宣宗为唐朝的中兴之主,因为他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的疾苦,和汉宣帝的情形相似,汉唐这两个谥号“宣”字的皇帝,和周代的宣王一样,都是中兴之主,还算是很不错的。
我们从后代历史上的事迹,可以证明孟子的话。一个朝代,在五六百年之间出了六七个圣贤之君,是很不容易的事。孟子又说:在商汤的时候,天下人心归向商朝,是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养成的,这种归顺服从的时间一久,一时是很难改变的。这可以说是人类的好习惯,也可以说是人类对历史的惰性。大而言之,一个国家民族对于自己历史文化的习性,是很难改变过来的;小而言之,个人的习性,也是很难改变的。想把一个旧的传统变过来,十分不易,而且传统愈久愈是难以改变。
接着孟子又说:所以到了由武丁领导天下的时候,能使诸侯都来诚心朝贡,好像也是轻而易举,像在手掌上运用的事情一样。即便到了末代纣王时,这位商朝最后也是最坏的一位帝王,虽然他很坏,但距离他的祖先、那位名王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的时代,并不太远。
上代商朝世家忠臣,遗留下来的好风气、好政绩、好政体、好制度并没有变,所不同的只是纣王个人的暴虐而已。同时,纣王时代辅佐他的同宗之中,或是纣王的叔伯,或是纣王的兄弟辈,还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等许多的贤人。只是商朝到了这个时候气数已尽,刚好传到暴虐的纣王手里,如果是由商朝宗室的这些贤人中任何一个来当帝王,那么周朝就起不来,也不可能革命了。因为这个时候,纣王宗室的贤人们都还在全心全力辅助商朝,所以纣王虽那么暴虐,周朝也要等待时机。
久而久之,等商朝的根基先自行崩坏、气势衰败的时候,周朝才能起来。除了历史文化上的时间因素之外,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天下领土皆属纣王,人民皆是纣王的臣民,商朝人众土广。而文王当时不过只有方圆百里的一点点领土,以及少数人口。以这样悬殊的现实力量,对抗历史久远的殷商王朝,便可理解周朝的崛起是多么的不容易。
势机运成功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刚才讲述孟子为公孙丑解惑的一大段道理,中间有好几处转折,有好几个理由。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说下来,公孙丑也插不上嘴了。如果以现在的谈话形式和技巧来说,一定是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逐项加以分析。古人没有这一套,用不着这样一条一条排列起来,因为听的人一听就知道了。现代人讲话,如果不分别列举,听话的人会指说话的人不合逻辑,没有条理,不聪明。不知道究竟是古代的人不聪明,还是现代的人不聪明,这实在很难定论。
到这里公孙丑还是插不上嘴,孟子继续讲下去,应该是讲到第四点了。
孟子这里引用的话非常好。公孙丑是齐国人,问的是假如孟子在齐国当政将会怎样,又引用了齐国的两个历史人物管仲和晏子到问题中来,更讨论到齐国称王于天下的事。虽然孟子一开头就说了公孙丑“子诚齐人也”,仅知有齐国而已。说到这里,他还是引用了齐国的成语来说明他的论点。
齐国是姜太公(尚)之后,文化相当浑厚。孟子说,你们齐国有句名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这两句成语是道家思想的结晶,经过孟子一引用,更变成后世的名言,成为哲学上一个不易的定理。
青年同学们,现在读《孟子》,对于这句话最好能够牢牢记住。我们幼年时读书,读到这一类美而又有至理的名句,便立刻熟读、立刻背诵,到老还是牢记不忘的。
这句成语是说,虽然你有聪明绝顶的智慧,但是客观环境还没有构成有利的形势,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也就是说,一个聪明人,因客观的形势不利,也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比如骑摩托车,不能在刹那间就到达目的地,一定要车轮转动的那一股势,发生动力,才能到达。如果没有这个“势”,而空想到达,那只有进精神病院了。
你虽然有了无比坚固的基础,还是要等待时机,才能发生功用。所谓时机,也就是现代所讲的“命运”、“机会”。机会不来,你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枉然。
我们现在看电视蛮舒服的,可是电视机由发明而到成为全人类的需要品,就要一段时间和机运了。所以发明电视的人并没有发财,后来的人捡现成而做电视生意的,反而发财致富,这就是时机的关系。在他来说,虽有发明的能力,但运气未到。
历史上很多发明家常有潦倒而死的结果,皆时运未通。可是后人利用他的发明,却大发其财。所以读了《孟子》这几句话,想到一些不逢时机的事情,不禁喟然而叹,却也不禁要点头一笑说,果然不错。就如以谈“空”为主的佛法,也是注重时机因缘,何况世事是一切有而不空呢!
不过,时机来了,不晓得把握,又有什么用?我常说第一流智慧的人,创造机会;第二流的聪明人,把握机会;而愚笨的人错过机会,失去了以后又不断抱怨。如同赶公共汽车,第一流的人,先买好票,先站在第一个位子等着,车子一到,首先上去,有舒适的座位。第二流的人,买好票,刚好能挤得上去。第三流的人,公共汽车开过了,他在后面跑步追赶,赶不上了,便在公共汽车后面的一团黑烟中大骂山门。不过世界上这一流的人居多,也许我们就在此辈之中吧!
古今中外,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都是因为自己没有乘势,或没有待时,或无势可乘,或时机早已过去,或是时机迟迟不来。这些也可归之于命运,所谓生不逢时,虽有才能也毫无用处。就好像算命的说命好运不好,命是帝王之命,可是始终轮不到你上座,一生倒霉运,又奈何?!
乘势与待时,确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不但个人事须乘势待时,家庭事、社会事、国家事、天下事莫不如此。即使有了智慧,有了基础,还是要乘势,还是要待时。
又如大家都知道宋朝有两位爱国诗人,一个是陆放翁(游),一个是辛稼轩(弃疾)。他们在少壮时代皆是意气凌霄、豪情万丈的人物,当时生逢乱世,国运艰难,也真有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气概。
但到了他们的晚年,一切的豪情壮志,都归到孟子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的哲理名言之领域了。所以陆放翁有一首诗《书愤》说:
早岁那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辛稼轩则有一首题为“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词:
壮岁旌旗拥万夫 锦檐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媞银胡箓 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 叹今吾 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东家种树书
由来才命两相妨
孟子引用了这两句齐国的谚语来说明当时齐国的势与时的情形。他说,“今时则易然也”,现在齐国的时机到了,齐宣王欲王天下,容易得很。
孟子替齐宣王算命,知道这正是行仁政王天下的时候;而这个时势,却不利于他自己。“明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正是儒家的精神,圣人的用心。孟子志在淑世、救世,不计较自己本身的利害。
他说以齐国当时的形势来讲,土地、人民的力量,与历史上的夏后、殷、周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当他们——夏后、殷、周兴盛起来的时候,领土的幅员还没有超过千里,而现在齐宣王的领土已经超过了千里;人烟稠密,农业生产发达,经济稳定,社会一片繁荣。到了这种地步,不必再扩充领土,也不必用心经营,招揽百姓。土地与人民这古代政权的两大资本,齐国这时都充足了,已经有很富强的实力,假使这时候齐宣王能行仁政而称王,谁也抗拒不了。
同时,孟子又指出齐国正是得时之利的时候。他说,以历史时代而言,从周文王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在这么长久的年代中,从来没有以王道政治来领导天下的王者。周朝只有在文王到成王这段时间是兴盛的,自成王以后,就衰败下来了。到了战国时期,老百姓都在紊乱或者暴虐政治下辗转流离,在痛苦呻吟中挣扎,尤其到了七百年后的现在,情况更加严重。
这时孟子又说了两句名言:“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后来,在中国文化中,这两句话经常被人引用,尤其在政治理论方面。肚子饿了的人,容易满足“食”的欲望,饭也好,面包也好,吃起来都觉得好。肚子饱的人,一天到晚山珍海味,吃多了、吃腻了,吃到后来,吃什么都觉得不好吃。同样的,“渴者易为饮”,口干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喝,沟水、马尿都是好的,渴极了的人乃至可以吸自己的血,舔自己的汗水。
这里,孟子以饥渴的情形来比拟当时老百姓对于良政的渴望,他并且引用他所崇拜的孔子所说的话——“速于置、邮而传命”,德化的流行散布,比驿站、车马传送命令还快。
这个“邮”字,和现代的邮政的“邮”是同一个意义。所以邮政这一制度远在周代已经有了,后来又改称驿站。不过,古代的邮驿是由政府办理、专门为政府传递公文的,老百姓无权享受这种制度的便利。我国自清末设置文书传递和私人通信的机构制度,便采用周代这种公文传递制度的“邮”。在孟子那个时代,交通方面最快的就是这种邮政交通了,如果在现代来比喻,则应该说犹如卫星转播一样的快速了。
孟子最后结论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像齐国这样有万乘战车的大国,如果出来实行仁政,天下百姓都会很高兴的。从春秋时代开始,差不多二三百年间,老百姓好像倒悬着,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如果齐国能够实行仁政,等于把倒悬他们的绳子解下,他们会欢喜不尽的。所以现在行仁政,较之古代事半而功倍。“事半功倍”的成语,就是从《孟子》这里习用而来的。《梁惠王》上下章的内容,也几乎全是记录孟子劝魏、齐两国国君行王道的重要。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宋朝理学初起的情况。当时,主力派的儒家学者极力尊崇孔孟,后来发展为宋儒的理学。他们自认是尧、舜、文、武、周公、孔子道统的传人,但是其他一般的学者并不同意他们的论点,认为他们是自我标榜、矫枉过正。所以后来写《宋史》的学者,便把儒家理学派定名为“道学”,把一般儒家学者定名为“儒林”。
在当时的儒林学者中,有一位名叫李泰伯的,对孟子有反感。因此另有一名儒士要向李泰伯骗酒喝,便作了两首讽刺孟子的诗送给他,骗来三天大醉。诗中有两句,可说是对孟子生平鸡蛋里挑骨头,“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
孟子当时为什么栖栖遑遑要游说魏齐行王道?这里就是孟子的答案,他认为这个时候是必须施行王道的好时机。也可以说,孟子确实认为当时需要革命,不必礼尊周天子了。因为当时周天子名存实亡,可能只有现在一个乡镇长那么大而已。大家给他饭吃他就吃,不给他吃他也只好坐在那个天子位子上等待,还欠了一身债。“债台高筑”这个成语,就是从周赧王来的。所以,孟子准备把尊周天子为“正统”的历史包揪甩掉。孟子当时所看到的,是天下老百姓的痛苦生活,因此他想要做的,是解救老百姓的痛苦。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完全是菩萨心肠,所以孟子早在当年就有民主、民权、民生的思想。下面就讲到孟子的学术思想。
不动心的哲学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公孙丑问孟子:老师!假使齐宣王请你当卿相,你的理想就可以实现了。在功成名遂的时候,你动心不动心?孟子说:不!我早在四十岁的时候,就到达了不动心的境界。
孟子说的是老实话,孟子和公孙丑谈这些话的时候,应该是再度到齐国,正是他已过中年了。他告诉公孙丑,早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对于任何荣耀困辱都可以不动心了。他学孔子真学得太像了。在《论语》中孔子说他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四十不动心,等于孔子的“四十而不惑”。
说到“四十而不惑”,想起一则笑话。在明朝时,有一个人读《论语》中孔子这段话,便作恍然大悟状,说自己读通了《论语》,有一大发现:原来孔子少时生了病不能走路,大概是小儿麻痹症,到了三十岁才能站起来,所以叫做三十而立;到四十岁两腿才有力量,可以随意走路了。这是一则讥讽书呆子的笑话,但也可见古今青年人的调皮都是一样的。
讲到孟子说的不动心,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他的“不动心”,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化讲学问、谈修养,关系太大了。
以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而言,孔孟思想的文化基础,历史最为悠久。从佛家角度讲,后来佛教的思想虽然流布中国,但已经迟于孟子五六百年;即使以最早的史迹计算,佛教最初于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也迟了孟子约三百多年。再以道家的文化来说,原始的道家并没有谈到“不动心”的问题,后世道家提出类似“不动心”的修养方法,也比孟子迟了四五百年。而儒家文化,后世的中国儒家,尤其是宋朝以后,理学家的一切修养,差不多都是以“不动心”为学问修养的中心话题。至于学佛的人讲修持工夫,也是与“不动心”有类似之处,只是名称不同,叫做不生分别,或不起妄念。所以“不动心”是很值得讨论的题目。但在讨论“不动心”这个中心问题之前,我们先问一个轻松的问题。
试问诸位,孟子说不动心的时候,你说他究竟动心没有?照逻辑论辩的方法来讲,他动心了。他在齐宣王、梁惠王面前拼命地鼓吹。如果他不动心,则又“何事纷纷说魏齐”?严格地说,悲天悯人,正是圣贤和大英雄的动心之处。所以说,什么叫做“不动心”,是很难下一个定义的。
唐宋以后,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儒家也好,各家做修养的工夫,都希望做到不动心。直到现在,学禅、学道,不管哪一宗派的修法,凡是讲究静坐工夫的,也都是希望做到不动心。只是唐代以后的禅,改变了一个名词,叫做“无妄念”或“莫妄念”。其实,名异而实同,换言之,后世佛家的修持工夫,更是强调不动心的重要。
佛学、禅学等,讲不动心的资料太多了,我们只取简单扼要而且有趣味性的来说。例如唐代诗僧贯休和尚的《山居诗》,便是强调不动心的代表作。他说:
难是言休即便休 清吟孤坐碧溪头三间茆屋无人到 十里松阴独自游明月清风宗炳社 夕阳秋色庾公楼修行未到无心地 万种千般逐水流
他这首名诗,代表了一般学禅者的观念,他一开始的意思便说哪一个能做到说放下就完全放下的?第二句以下是写真正出家人的修为,一个人冷冷清清,孤独地在高山之上、或在溪流清寂之处吟唱静坐,三间茅屋,十里松风,那是多么幽美的胜境。月明之夜,夕照秋林,也正是最好的良辰美景。但此时此地外境虽然清净,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无心才算是真清净;如果“修行未到无心地”,这些净境也只有徒添愁思,修行也是白修,真是“万种千般逐水流”了。这两句是直接说明修行不达到这种不动心的无心境界,一切的一切仍然是随波逐流而去,不足道也。
这是利用贯休和尚诗句的文学境界,来说明禅宗乃至佛学其他各宗派的原则,都是着重在不动心的一面。这首诗比任何佛学的术语或经文的解释,都更为简单明了。
此外,明代有名的诗僧棺堂也有一首诗:
心心心已歇驰求 纸帐卷云眠石楼生死百年花上露 悟迷一旦镜中头人言见道方修道 我笑骑牛又觅牛举足便超千圣去 百川昨夜转西流
“心心心已歇驰求”,这就是讲不动心,一切的妄心都已真正的空去,此心再也不向外面去驰求乱跑。
“纸帐卷云眠石楼”,这要真正有道行的人才做得到,普通人做不到,勉强去做,一定会伤风感冒。过去有许多修行人,住在高山顶上的石洞里,连窗子都没有,云雾随时可以进来,潮湿得很;一层层的云气,又冷又重,绝非都市里的大厦可比。
“生死百年花上露”,这是指生命的短促。活了一百年,算是上寿,但是以整体生命的历程看来,这百年的人生只是分段生死的一节,也只不过像早晨花瓣的露珠一样,太阳一升起,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了。
“悟迷一见镜中头”,这是引自《楞严经》中的典故。在《楞严经》中,释迦牟尼佛说了一个故事:有个人名叫演若达多,一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看到镜子里面有一个头,心想我自己的头到哪里去了?愈想愈不对,看不见自己的头,因此他疯了。等到他有一天再照镜子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头原来仍旧在自己身上,他才恍然大悟,不再发疯了。人,只有这样一条自救之路,所以悟与迷的道理就在这种地方。自去迷,也自去悟,说佛在哪里,你本来就是佛,只是你没有找到自己而已。
“人言见道方修道”,一般人都说,求到了法,见到了道,才开始修道。“我笑骑牛又觅牛”,人本来就在道中,何必再去求道见道,这等于骑在牛背上还要去找这头牛。如果懂得骑牛觅牛是错误的,那么“举足便超千圣去”,一下子就超过了儒、释、道三教的圣人境界,自己自然就是一个平平实实的本来人了。“百川昨夜转西流”,这是倒过来说的。
以前中国人说“天上众星皆拱北,人间无水不流东”,天上的众星都是拱卫着北斗星,这是不错的。至于“人间无水不流东”,是中国人的话,在其他的地区来说,也可能是“人间无水不流西”。而棺堂这句诗,并不是指现实世界的川流而言,只是作诗的一种“比兴”技巧,指修道而言,只要反求诸己,一夜之间即可还我本来。
佛家的这些文学作品,是不是都代表了不动心呢?尤其学禅的人,更喜欢大谈《六祖坛经》的“无念”。“无念”不就是“不动心”吗?学佛修道做工夫的人,打起坐来,盘腿固然困难,想“不动心”更是做不到,这是最痛苦的。要做到不动心是很困难的。
孟子说自己四十岁已经做到了不动心,依照这样计算,他大约做了二十几年的工夫。从孟母带他三迁,长大成人后,他一直走圣贤之路,起码花了二十多年的工夫,才做到不动心的境界。后世的理学家们,大部分都只注意孟子这里所谓“不动心”的工夫和“不动心”的境界。
不过我们要了解一点,公孙丑是问孟子,如果你做了齐国的宰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功成名遂的时候,你动心不动心?这好比我们如果访问美国总统卡特(当时的美国总统),问他由花生农夫而当选美国总统,动不动心?卡特是美国人,他一定说:“我很高兴,非常兴奋,当然动心啊!”这也是西方人可爱之处。如果问到中国人,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多半是说些谦虚的话,才算是有涵养,所以最多是说“没有什么!”“诚惶诚恐,勉为其难”等门面话而已。
全部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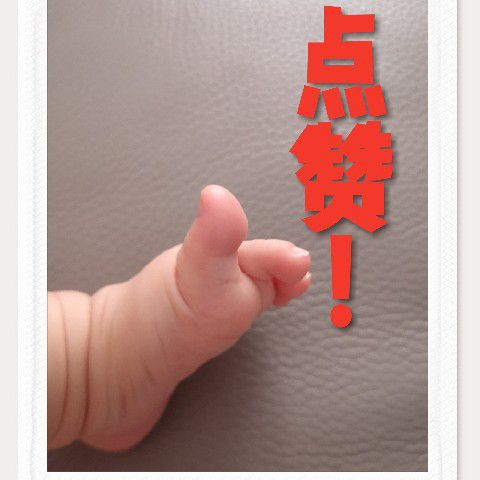
吴石跋幽十六
· 江西老子只花了三秒就达到了不动心的境界。
暂无更多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