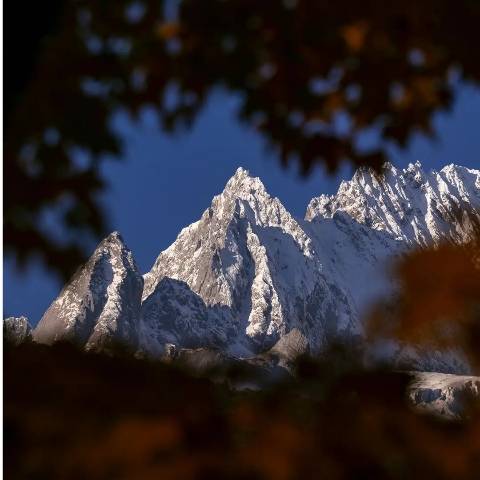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南怀瑾先生:不动心并不是无情,而是不受一般私情、情绪的困扰
唯大英雄能本色
现在我们读的《公孙丑》这一篇,是绝妙的文章,这篇先从一顶帽子开始,由公孙丑问孟子功成名就时动不动心。这不是我们平常问的你高兴不高兴。动心和高兴程度不同,公孙丑这里问的是动心不动心,这是个大问题。
人谁不动心呢?尤其是面临功名富贵时,如何能不动心?孟子这里说“四十不动心”,这是个主题,人怎么做到不动心呢?人啊,天天随时随地在动心,怎么个动心呢?《中庸》里面就提到“喜、怒、哀、乐”,这是孟子的老师子思把人的心理状况归纳成这四种情绪。后来演变成中国文化里常提到的“七情六欲”。六欲是汉朝以后佛学传人的思想,是说人对色、声、香、味、触、法的需求。七情呢?是我们固有的文化,出自《礼记》,除了“喜、怒、哀、乐”之外,又加上“爱、恶、欲”。不管七情也好,八情也好,不去管它如何分类了,我们每天对事情没有不动心的。人真修养到“不动心”啊,就是“内圣”境界,不但对功名富贵不动心,—切都不动心。那么,你会说,不动心不就是死人一样,不就是呆了吗?所以我们要讨论不动心。
其次,由不动心引出来公孙丑的一段话,他说:老师,你的不动心,有这样高的修养工夫啊!秦国当年在秦武王时代有个勇士叫孟贲的,你比他还要厉害啊!
从公孙丑这句问话我们发现,这位学生到底不行,公孙丑竟然拿武功来比孟子的不动心。武功里有没有不动心呢?有。现在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方才也提到过,打拳啊、练武啊,叫国术。中国过去不用这个名称,什么“国术”、“同技”的,是民国初年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才改用的名称。古代对于文章写得好、武功练得好,称文艺、武艺,意思是好到了艺术的境界。我们看古代的书,说“武艺高强”,不说“武功高强”,更没有说“武术高强”的。虽说只是用字的不同,但用字涉及一个国家文化思想的背景。所以武功到了最高处,同文学一样,进入了艺术的境界。过去的武艺也的确先要修养到不动心。那么孟子由这个问题提出两个人,一个北宫黝,一个孟施舍,来加以说明,而后再转人修养方面。他说北宫黝武功修养的原则像子夏;孟施舍的武功修养像曾子,原则是“量敌而后进”,比北宫黝高。这里第二个重点来了,他说曾子“守约”,讲到修养的方法了,什么叫“守约”?
门户之争的动心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不动心”这三个字。由于在座许多人对“不动心”非常动心,下课后纷纷提出讨论,所以我们再来谈谈。前面提过,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大体上可分为两截来看。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是儒、墨、道三家的天下,严格说来,道家是最古老的。到了汉朝佛教传入以后,文化结构变成儒、佛、道三大主流,而且由三大“家”变成三大“教”。儒家到了唐末还没有正式变成儒教,经过了唐、五代,一共四五百年的酝酿、转化,直到宋朝,才真正变成了儒教的典型,这是因为理学家的原故。如宋初的五大儒,程颐、程颢两兄弟,张载、朱熹、陆象山等,都是有名的理学家。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在宋朝初期那个阶段,走入一个新潮派的学术思想——理学,反对佛家以及道家。而在隋、唐、五代时,整个思想、学术界都是禅宗的天下。
去年我在东海大学有个唐代文化的专题讲演,我说唐代三百年间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义理之学根本谈不上,至于辞章之学,唐朝是文学好,有名的唐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但是谈到学术思想则没有。其实应该说有,只是都走入了佛学和禅宗的领域。这个学术思想界的怪现象一直延续到五代,所以这三四百年的文化思想可以说整个是禅宗的天下。在这个情势下,除了道家还分得小半天下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了。儒家呢?只有八个字,“文章华丽,记闻博雅”而已。有一点必须声明,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站在佛学与哲学的立场看,唐代却是文化思想的鼎盛时期。
这个情况延续到了宋朝,自然就非变不可,新潮派的学术思想非起来不可,因此有宋朝五大儒的前后兴起。但事实上,宋明理学家应该说是“外儒内禅”,外面打着儒家的招牌,喊着儒家的口号,但内在修养、工夫却非禅即道。所以我常对宋明理学家有所论议,认为他们风度太差,明明是向佛道两家借用的东西,而且还一边借一边偷,然后反过来就骂这两家。而这两家可没有还手,你爱骂就骂。相形之下,更让人觉得理学家的态度不够潇洒,胸襟不够开阔,讲圣贤之学术却无圣贤之气度,实在是件遗憾的事。
宋儒修养工夫的境界,却也标榜“不动心”。怎么叫“不动心”呢?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人谁能不动心呢?我们都知道佛学把人的思想称为妄想,妄想也就是烦恼,一切众生都因妄想而来,所以一切众生生来都有烦恼。我常觉得佛学里烦恼这个名词翻译得实在是高明。烦恼不是痛苦,我们脑子里永远有许多连续不断的游丝妄想牵扯着、困扰着我们,这就是烦恼,烦恼是由妄想而来。为什么不叫它是思想呢?思想这个名词连起来用,是唐以后才有的,到了近代才流行。追根究底,它来自佛学,但在佛学里,思是思,想是想,不可一概而论。思想不一定是妄想,但是我们一般人平常思想都是妄想,因为这些“想”都不实在、不稳定,停留不住,保持不住,随时跟着外境、生理、气候、环境等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叫它做妄想。要做到妄想而不动心,真是谈何容易!
道家在唐以后变成道教,差不多也是用“妄想”这个名词。所以说唐朝以后,道教实在和佛教已经分不开了。如果站在比较宗教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门很新的学问,在美国有些大学乃至研究所有开比较宗教学的课程,把各个宗教的内涵和形式以及哲学基础,作一番比较研究。佛教和道教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我们知道佛教里人和人见面就说“阿弥陀佛”,这句话很有意思,后来演变成中国文化里的常用语。平常讨厌一个人,一旦看他跌了一跤,觉得开心、活该,于是顺口就说“阿弥陀佛”。好朋友病了,心里难过、悲伤,也说“阿弥陀佛”。好的说“阿弥陀佛”,坏的也说“阿弥陀佛”,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真好。尤其在大陆,过去到庙子里看到和尚,问他吃过饭没有,他说“阿弥陀佛”;你好吗?他也说“阿弥陀佛”;不好吗?他还是说“阿弥陀佛”。反正不着边际,这真高明。道士们见面呢?不说“阿弥陀佛”了,他们说“无量寿佛”,是从佛教里翻译来的,“阿弥陀佛”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无量寿佛”。佛教里还有一部《观无量寿佛经》。所以你说他究竟是道教呢?还是佛教呢?搞不清楚,我觉得蛮好玩的。
严格地说,理学家和禅与道也几乎分不开。我们举个例子,就说“不动心”吧,怎么个“不动心”呢?我们看看供在台北指南宫那位有名的吕纯阳,他有一首诗:
一日清闲自在仙 六神和合报平安丹田有宝休寻道 对境无心莫问禅
据说这是吕纯阳没有悟道时候的诗,但是他工夫已经很好了。据说这时他能坐着他自制的直升机--飞剑,在空中飞来飞去。飞来飞去这只是工夫,还没有悟道。但他这首诗也可以说是讲修养的,你看他说的“一日清闲自在仙”实在是好,我们如果能够有一天不忙碌,呆在家里,没有事,没有烦恼,那就好比神仙。但是一天偶尔没有事,在家休息,也许做得到;可是我们尽管清闲,却不见得自在:放个假在家,东搞搞,西搞搞,老婆儿子哭一顿骂一顿,真不自在。“小人闲居为不善”,清闲反而危险,所以说能清闲自在也不简单。
第二句“六神和合报平安”难了,身体一点病痛难受都没有,“六神和合”是身体的,精神健旺,那谈何容易!这时“丹田有宝休寻道”,道家讲炼成丹就成仙了,他们认为每个人内部都有“丹”,就是长生不老的药,但是一般人找不到。现在吕纯阳找到了,他牛吹大了。第四句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有关了,“对境无心莫问禅”,这个境界多大啊!如果人真做到“对境无心”的话,的确就可以成佛,也就不用参禅,不用学佛,不用修道,已经到家了。
现在问题来了,他这“对境无心”和孟夫子讲的“不动心”是一样的吗?现在我们不管他“对境无心”也好“不动心”也好,再回过头看看一般学佛修道的,打起坐来,都希望做到“无妄想”。那位鼎鼎大名的禅宗六祖,曾经标榜禅宗以“无念”为宗。什么叫无念呢?就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那么和孟子的“不动心”是不是一样的呢?它们的含义似乎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孟子的“不动心”,重点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勉强说,是佛学里“事理无碍”的初阶。而佛学里的真正“无念”,除了“事理无碍”以外,还涉及“理无碍”、“事无碍”、“事事无碍”等,包括了形而上本体的实相,以及形而下修为的原则。详细说起来,又是一个大专题,我们就此略过。
虽然两者之间有程度和层面的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说,这种修心养性之道,不是后来佛教传入以后才有的,早在孟子提出“不动心”之前,中国文化里就有了。这套“内圣外王”的修养,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精华,和西方文化比较起来,的确有所不同而别有独到之处。
从心所欲的不动心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研究一下《论语》,孔子没有提出“不动心”的问题,但是讲到过类似的修养。我们看他老人家的报告“四十而不惑”,不惑相当于不动心。但是真正能圆融地不动心、到达圣人境界,是他七十岁时,“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时孔子才完成了圣人境界的修养。我们由孔子的自我报告,可见“不动心”鉴别之难。
现在我们大概对“不动心”这个名称所包括的与我们有关的内容作了一番研究,竟有如此之多,详细发挥起来,几年都讲不完。道家、儒家、佛家修养到不动心的理论以及方法,介绍起来太多了,现在我们还是限定在孟子的“不动心”来说。真正的“不动心”是什么样子呢?孟子举出两种典型。一种是属于外型的“不动心”,就像武术家一旦身陷重围,成千成百的枪杆对着,但是他眼睛都不眨,视死如归,一点不动心。普通一般人可做不到,尤其小姐太太们,遇到一点小事就尖声大叫,十里外都听得到。实际上女性们尖声大叫,你说她真怕吗?不见得,她就是爱叫,这一叫啊!把男性的“不动心”就给叫动了。
记得当年在大陆,我曾经去庐山住过,那里有座寺庙叫天池寺,旁边有个深谷,可以说是万丈悬崖,看下去令人头晕目眩,很少有游人到此。那里有块石头就像舌头一样,突出山壁,石头的大小,正好两只脚可踏在上面。据说这块石头只有两个人踏过,一个是王阳明,他站在这块突出的小石头上,向万丈深渊下面望去,试试看自己恐惧不恐惧。另外一个人是谁呢?是蒋公中正,他一生研究王学,所以到庐山时,也到那块石头上站一站,就是想看自己面临这样的险境是不是会动心。
置身危难重重的闲境而能不怕、不惧,算不算是不动心呢?这还不能算是孟子所讲的真正“不动心”,这还只是对外境的不动心,就像孟子所列举的那两位武士北宫黝和孟施舍的修养一样。那么孟子所认为真正的“不动心”是怎么样的呢?他认为要像曾子那样,中心要有所主,也就是所谓的“守约”,内心要有所守。不动心并不是一个死东西,假如一旦父母死了,我们还在那里学圣人不动心,这成什么话呢?如果不动心就是无情的话,那么父母儿女可以不管了,国家天下也不相干了,这个样子的“不动心”还能学吗?自古以来,很多学佛、修道的都误以为“莫妄想”是不动念头,是究竟的真理,因而导致一种非常自私的心理,凡是妨碍打坐、用功的,都是讨厌的,都是不应该的。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想做,也不肯做,就只是闭眉闭眼的要不动心。其实他又要成仙,又想成佛,欲望比一般人大得多,你说这颗心动得有多厉害!可是一般修道的人往往都忽略了这正是动心,还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在不动心呢!
昨天一个朋友来,我和他谈起不动心的事,提到我最近写的两句诗——“事于过后方知梦,浪在波心翻觉平”。中国文学上我们常看到“人生如梦”这四个字,在境界上看来多美,多洒脱;但在我看来,并不以为然,我看他和我一样,都是事后的诸葛亮,过后方知,人在身临其境时并不知道。就好比掉在海里,陷到大浪的中心点时,或者困在台风眼时,反倒觉得没有一点风,也没有一点浪;坐在飞机舱里,坐在快速火车上,自己反而不觉得在动。所以许许多多讲儒家修养的以及学佛修道的人,把两腿一盘,眼睛一闭,打起坐来,清清净净的,自以为是“不动心”了、“无妄想”了,其实正是“浪在波心翻觉平”。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大妄想就是要修道,正在动心啊!这正如佛经上所形容的,“云驰月驶,岸动舟移”。
如果我们把不动心认为是个死东西,那就完全错了,如果认为修养到“无念”的境界就算得了道,那更是大错特错。现在反过来看看普通一般人的思想,总是连绵不断的,一波未平,数波又起。就算打起坐来,一直告诉自己要“莫妄想”,也还是无可奈何!我们多半都不习惯说实在话,如果肯说实话的话,我们请一千个学道、打坐了几十年的人来问问看:静坐时,有没有妄念呢?我相信有九百九十九个半的答案都是“有妄念”,都没有办法做到无妄念。如果说修养到了没有妄念,那很可能是像我前面所说的,“浪在波心翻觉平”,只是自以为清净无念罢了。
因此我们要注意,孟子的话没有错,他以他的太老师曾子为不动心的典范。曾子不动心的原则就是“守约”,所谓“守约”,是心中自有所守,有个定境,有个东西。因此要“约”,约住一个东西,管束一个观念,照顾住一点灵明。我们平常的思想、情绪都是散漫的,像灰尘一样乱飞乱飘。我们这边看到霓虹灯,马上联想到咖啡厅,接着又想到跳舞,然后又想着时间到了,必须赶快回家向太太报到。一天到晚,连睡觉时思想都在乱动,精神意志的统一、集中简直做不到,所以必须要“守约”,守住一个东西。
专于一 万事毕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宋明理学家标榜“主敬”、“存诚”的道理,这也可以说是他们的高明处,没有宗教气息,只以“主敬”、“存诚”为宗旨。什么叫“主敬”、“存诚”呢?这也就是本篇下面一节孟子所提到“必有事焉”的道理。好比人们欠了债,明天就必须还,还不出就要坐牢。但是今天这笔钱还不知道在哪里,于是今天做什么事都不行,听人家说笑话,笑不出,人家请客也吃不下,这种心境就是“必有事焉”。又好比年轻人失恋了,不知在座年轻人有没有失恋的经验,假如有的话,那个时候一定也是放不开。至于谈恋爱时,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像《西厢记》所说“茶里也是他,饭里也是他”,到处都是他的影子。这就是曾子所谓的“必有事焉”。我说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我们做修养工夫,如果真做到心里一直守着一个原则用功的话,那就上路了。
每个宗教对心性的修养,都各有一套“守约”的办法。譬如佛教要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必有事焉”的原则。密宗的这个手印、那个手印的,东一个咒语、西一个咒语的,也同样是“必有事焉”。又如天主教、基督教,随时培养人们对“主”、“上帝”的信念,乃至画十字架,也都是“必有事焉”的原则。说到天主教的手画十字,很有趣的是,密宗恰好也有画十字的手印,与天主教所画先后次序不同。这两个宗教的手印到底是谁先谁后呢?实在很难研究的。现在不管这些,我们只专对学理来研究,把宗教的外衣搁下。每个宗教教人修养的方法,都是运用“必有事焉”的原理,也就是孟子所讲“守约”的路子。
我们是现代人,就先从心理状况来作一番研究。我们在每天乱七八糟的心境状态中,要想修养到安详、平和、宁定、超越的境界,是很难的。首先必须要训练自己,把心理集中到某一点——这是现代的话。佛教的“阿弥陀佛”、孟子的“守约”以及现代的“心理集中到一点”,是没有两样的,融会贯通了就是这么个东西,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道理、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用词不同罢了。不论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真讲修养,就必须先做到“守约”。佛教所谓的入定,也就是“守约”的初基。所以孟子讲不动心的修养工夫,第一步就必须做到“守约”。如果就佛学而言,要修养到不动心的话,第一步就必须先做到“定”。“定”的方法是怎么样呢?照佛学原理说来,就要“系心一缘”,把所有纷杂的思绪集中到一点,这就是“守约”。如果发挥起来详细讲的话,那就多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孟子认为修养到不动心,必须先做到心中有所主。
在座诸位有学禅的,有念佛的,有修道的,有信其他各种宗教的,或许有人会问:我坐起来什么也不守,空空洞洞的,好不好呢?当然好。但是,你如果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守的话,那你就错了,那个空空洞洞也是一个境界,你觉得空空洞洞的,正是“守约”。和念佛、持咒、祷告等同样是“系心一缘”,只不过现象、境界、用词观念不同。
如果真正做到不动心的话,那就动而不动、不动而动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明朝潘游龙的《笑禅录》,里面有一段提到一个秀才,到庙里拜访某位禅师,这位禅师懒得动,坐着不理他。秀才心直口快,就问他为什么坐着不起来。这位禅师就说:不起即起。秀才一听,拿起扇子在禅师的光头上一敲,禅师气得问他:你怎么打人?秀才就说:打即不打。潘游龙在这部《笑禅录》里,用禅宗的手法列举古代的公案,重新参证。他用轻松诙谐的题材,使人在一笑之间悟到真理。可惜胡适之先生竟误会《笑禅录》是部鄙视禅宗的书,所以引用它“打即不打,不打即打”来诬蔑禅宗,反倒令人失笑了。
如果真修养到不动心的话,那倒真是“不动即动,动即不动”了。这话怎么说呢?就是对一切外境都非常清楚,对应该如何应对也非常灵敏,但是内心不会随着外境被情绪所控制。这就是庄子所谓的“哀乐不入于胸次”。但是要注意,不动心并不是无情,而是不受一般私情、情绪的困扰,心境安详,理智清明。如此才能步人“内圣外王”的途径,才能为公义、为国家、为天下贡献自己。
中国这几千年来丰富的文化思想、多彩多姿的历史经验,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这的确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地方。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平常人品很好,但是一旦到了某个地位,就经不起环境的诱惑,而大动其心了;相反的,一旦失意,也经不起失败的打击,于是也大动其心了。现在在座的青年,看起来一个比一个淳朴可爱,但是有一天到了“哼啊!哈啊!”的显要地位时,或者变成一个大富翁时,周围人一捧,那时如果没有“守约”的工夫,那你就不只是动心了,而是连本有的平常心都掉了,昏了头了,这样自然就随着外境乱转了。
如果没有经过时间、环境的考验,很难对一个人的品德、修养下一个断语。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我积一生的经验,对这几句话体会很深,许多人可以做朋友,但是进一步共同做事业,或者共同学道,那就难了。又说“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以共学,也可以适道,可以共事业,但不能共成功,无法和他共同权变,不能给他权力。如果共同做生意,失败了也许还能不吵架;最怕的是生意赚了钱,分账不平,那就动了心,变成冤家。我常对朋友说:你的修养不错,差不多做到了不动心。不过,可惜没有机会让你试验,看看一旦有了权位是不是还能不动心。人到了一呼百诺这种权势,连动口都不必,话还没说出口,旁边人就已经服侍得周周到到的了,这种滋味当然迷人,令人动心。所以要修养到“守约”、“不动心”,的确是圣人之学。我们如果详细讨论的话,还多得很,牵涉到古今中外儒、释、道三家各种的修养。
全部回复

评论区开荒,我辈义不容辞
来抢第一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