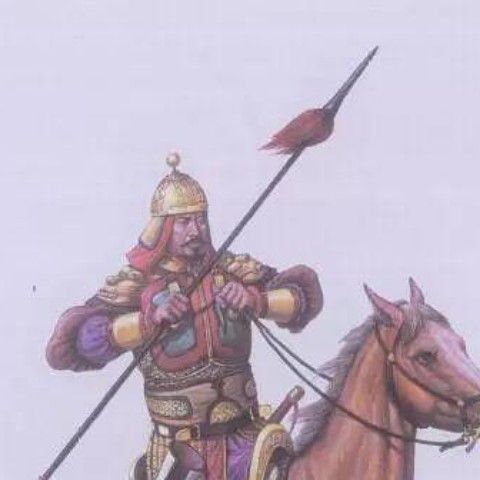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历代宦官的管理制度(文录摘自于《佞幸:中国宦官与中国政治》)
自秦以来,历代对宦官的管理,除设置衙署与定官号、职掌、级别如第一节所述外,尚有收选、出宫(情况均见上文有关章节)、服饰、各种禁令、升迁、奖惩、休沐致仕、婚娶养子等其他方面的管理制度。其繁简程度虽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不外是为了禁止宦官干预政事,抑制他们势力的发展,规范他们忠于职守,做驯服的奴仆。下面我们对此分别予以概述。
服饰制度
在封建社会里,舆服的不同,标志着等级身份地位的差异,因而受到重视。历代对宦官的服饰,均有具体的规定,但亦随时变易。秦、西汉时,一律银铛左貂。东汉时,改为金铛右貂。金比银贵重,右比左更尊,这一服饰的变化,反映了宦官地位的提高。再如佩刀,君主刀剑鞘用雌比银贵重,右比左更尊,这一服饰的变化,反映了宦官地位的提高。再如佩刀,君主刀剑鞘用雌黄色,诸侯王公百卿用黑色,而小黄门亦用雌黄色,标示了他们近侍君王的特殊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皇权的表征。唐代,宦官最早是穿黄绢衫,其后章服品第与外廷同。两军诸司内官,不得着纱縠绫罗衣服;内官不得朝服助祭,只能依所兼正官,从资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但唐后期宦官势力膨胀,服饰上的限制遂被打破,如祀圜丘,“故事、中尉、枢密皆衫侍从。僖宗之世,已具襕笏”,即从穿整套衣裤改为穿袍子。“又令有司制法服……于是宦官始服佩剑侍祠”,以致“中官皆如宰相大臣朝服”,百官抗议均无效。在《金石萃编》收的墓志中,还可以见到宦官亦受赐紫金鱼袋。宋代,内臣自内常侍以上及入内省与内侍省内东、西头供奉官等,既参加朝会,亦要穿朝服。其朝服,自内常侍以上,冠服各从本等,寄资者如本官。入内省与内侍省内东、西头供奉官为第七等,均二梁冠,方胜练鹊锦绶。高品以下服色,依古色。系印绶的带子,朝服、祭服的蔽膝,鞋的颜色,与衣服同。景德三年(1006),诏内诸司使以下出入内廷,不得服皂衣,违者论罪。内职亦准许穿窄袍。公服,即常服,沿袭唐朝,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幞头,平角,初用藤织草巾子为里,外面蒙上纱,再涂漆。笏,象牙制。每年赐百官锦袍时,入内押班、内侍副都知押班等,均可得公服、绫汗衫。
由于宦官身份特殊,其服饰名色很多不为外廷所知,故下面以明、清两朝为例,加以介绍。
明代,太祖朱元璋强调:“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所以甫有天下,便命儒臣稽古讲礼,定官民服舍器用制度。吴元年(1367),定内使冠服制:凡内使冠用乌纱描金曲角帽,衣用胸背花团领窄袖衫,乌角束带,靴用红扇面黑下桩。各宫火者衣服,与庶人同。洪武三年(1370),重定内使服饰之制。谕宰臣:“凡内使监未有职名者,当别制帽以别监官。”于是礼部定拟:内使监官凡遇朝会,照依品级具朝服、公服行礼。其常服,葵花胸背团领衫,不拘颜色。乌纱帽,犀角带。无品从者,常服团领衫,无胸背花,不拘颜色,乌角束带,乌纱帽、垂软带。年十五岁以下者,只戴乌纱小帽。得到允准 。
永乐以后,在皇帝左右近侍的宦官,都穿蟒服,其形状和长袍一样,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次一等的则穿飞鱼服。弘治元年(1488),都御史边镛奏称:国朝品官没有穿蟒衣的规定。蟒无角、无足,与龙的形状相似,臣下穿蟒衣不符合制度。于是孝宗诏令禁止,并禁玄、黄、紫、皂、柳黄、明黄、姜黄等颜色。但因积习相沿已久,故实际上是禁而不止。
太祖时,内臣服无朝冠、幞头,亦无祭服。万历初年,穆宗神主进入太庙,司礼太监滕祥、孟冲、陈洪戴进贤冠,穿祭服跟从,这是他们自己擅自制作穿着的。但万历时,也只有司礼掌印受命祭祀中溜、灶井之神之夜才穿。到了天启时,凡皇帝万寿节、年节,从掌印到牌子,全都是朝服朝冠,在乾清宫大殿或内陛上,照外廷仪注行庆贺山呼礼。这时内臣的朝服、朝冠、带履,与外廷众臣,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刘若愚在《酌中志》里,对万历以后宦官的服饰、舆马,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大致如下:
贴里: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乾清宫管事牌子,各执事近侍,穿红贴里缀本等补。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长官,随内使小火者,俱得穿青贴里。十月初四到次年三月初三,穿纻丝;三月初四到四月初三,穿罗;四月初四至九月初三,穿纱;九月初四到十月初三,穿罗。遇闰月则增加十日,由司礼监预先题奏传行。凡婚庆吉典,则虽在夏秋,亦必穿纻丝供事。若羊绒衣服,则每年小雪之后、立春之前,随纻丝兼穿。凡大忌辰穿青素,祧庙穿青绿花样,修省亦穿青素。按旧制,夏穿的青素是屯绢;冬穿的青素是玄色的纻丝。万历时,在蟒衣贴里之外,又创制了一种叫“喜相逢”的式样。前面织一黄色蟒,在大襟向左,后有一蓝色蟒,由左背向前,两蟒恰如偶然相遇、相望戏珠之态。这是举行婚礼时,宫中贵近太监所穿。:其形状是后襟不断,两旁有摆;前襟两截,下有马面褶,从两旁起。司礼监写字以至提督,其他衙门的总理、管理,都可以穿。红色的可以缀本等补。
圆领衬摆:其制作与外廷相同,各按品级穿着。凡司礼监掌印、秉笔、乾清宫管事之积有年劳者,可以分别得到赐坐蟒补、斗牛补、麒麟补。凡请大轿长随及都知监,戴平巾。有牙牌的,穿狮子、鹦鹉杂禽补。
二色衣:在皇帝跟前的人所穿的衣服,最外一层是盖面,如、贴里、圆领之类。第二层是衬道袍。第三层是缀领道袍,其缀领用白浆布做,可以拆换,只有入过皇城的人才能缀。这三层里面或袄、或褂,都不许露出白色袖口或脖领。二色衣,指夏天用葛布做上身,以深蓝或玉色纱做下褶,领、袖亦各接上一寸或数寸,以便拆洗,并避免在皇帝跟前露出白色。
官帽、平巾、圆帽:官帽,俗称刚叉帽,用竹丝作胎,蒙以真青绉纱,供奉御至太监戴。平巾俗称砂锅片,亦用竹丝作胎,蒙以真青罗。形状如同官帽,但无后山,只有长尺余的一幅罗垂在后面,供长随、内使、小火者戴。皇城内臣还可以戴圆帽,冬季用罗和纻制造,夏天则用牛尾、马尾、人发,俗称为“瓜拉”。
披肩、暖耳和围脖:披肩,用貂皮制一高约六七寸的圆圈,大小和帽相似。两旁对应耳朵的位置各缝制一条皮毛的长片,毛向里,至耳,即用钩带斜挂于官帽之后山子上。供掌印至暖殿牌子戴。暖耳,用玄色素纻作一圆箍,二寸高,两旁用貂皮,长方,大小和披肩同。供提督至司礼监写字戴。绒纻围脖,形状和风领相似,但比较窄小,供内官内使戴。
束发冠:用金累丝造,上嵌睛绿珠石,四爪蟒龙在上盘绕,下加额子一件,左右插上长长的雉毛,每座价值数百至两千金不等。熹宗出游时,从司礼掌印王体乾至暖殿牌子全都戴上。
带:内使、小火者无带。请轿长随、都知监长随束角带。奉御以上束金镶玳瑁或犀带。太监以上得到特升,则赐给玉带,其款式冬则光素,夏则玲珑,三月、九月则顶妆玉带。
棕靸和靴:棕靸由巾帽厂制造,每年第一次冬雪时,便送司礼掌印、掌东厂秉笔每人两双,管事牌子每人一双,以便在雪地上急行。靴用皂皮制造,底软衬薄,里面是布,形状与皇帝履相似,但前缝少棱角,各缝少许金线。但当差内使、小火者一般不敢穿,只穿青面单布鞋、青布袜。
扁辫、油靴:扁辫是用绒的废料织成,长丈余左右,阔三四寸,形状像带子,比较松软。在下雨下雪时,将衣服撩高离地八九寸,用它来束住。油靴可以防水,供雨雪时穿用。
笏:象牙制,形状和朝臣用的相同。
牙牌、乌木牌及牌穗:奉御、长随以上戴牙牌,用象牙制,上有云尖,下方微阔而上圆,重六七两不等。上刻部门、职衔、忠字某号及不许借失等字。乌木牌是内使、小火者所戴。牌的形状是荷叶头,圆径二寸左右。一面刻内使或小火者字样,一面用长方火印篆文“关防出入”于中,火印两旁分刻内字或小字某号。牌穗用象牙或牛骨作管,青绿线结宝盖三层,直径约二寸,下垂长约八寸的红线,内悬牙牌或乌木牌,上有提系青绦。凡穿圆领随侍,及有公差、私假外出,在本等带的左面,便悬挂这牌穗。穿、贴里的,在宫中亦戴。天启时,又创制了印绶,和外廷官员一样,掌一印的佩一绶,像王体乾这样掌三印的,则佩三绶。
此外,还有各种有关服饰的赏赐,亦不为外廷所知。如“抹布”,其名称很不雅。其实宦官所佩戴的抹布并不是布,而是染成柘黄色的素纻丝或绫,长五尺,阔三寸,双层,方角,有点像宽大的带子,但没有穗。凡乾清宫管事牌子,暖殿,御药房、御茶房管柜子,御司房管库、管弓箭,请小轿四执事牌子,钦安殿、隆德殿、英华殿陈设近侍等,得到赐予的,才能佩戴在贴里的右面,而蟠结绦上双垂下来,露半条在外面,垂的长度与衣服齐。
刀儿:亦是得宠近侍的配饰。刀儿里面是一双小的象牙筷,一把小尖刀,长约六七寸,外面套上银镶鲨鱼皮等鞘,然后用红绒辫系束在衣左面牌穗上。刀儿和抹布,都是外衙门所不敢想望的赐品。宦官中有年资深而又得宠的,还可以获准在内府骑马、坐凳杌和板。
骑马:太监得赐玉带后,再升,则可以在内府骑马。骑马的范围限于东西下马门至北安、西安门栅栏、东上北门;东上南门至南内西上南门及宝钞司。有名骑马的,在万寿节等还要进马,情况见第二章第一节,此处不加赘述。
凳杌:司礼监掌印、秉笔中,年高而又得宠的,方能乘坐。其形状似靠背椅,在两旁加杆,用皮绑上,前后各有一横杠。抬的人在杆外斜插杠抬而正行。所以称杌,表示在禁地不敢乘轿。
板:其制作像床面一样,高四五尺左右,在靠后的地方安一椅圈,前后用粗绒绳拴住,用两条杠斜插着抬走,离地面一尺左右。这板不是钦赏的,也不算等级,是年老的司礼掌印、秉笔私自制的。其活动范围是乾清门外至西华门、东华门等。
内使凡遇节令及山陵等处有公事要外出时,都乘驴。嘉靖七年(1528),御马监提出,革退的马数目不少,请兵部将之拨归内使使用,得到准许。从此内臣公差才正式骑马。
天启年间,宦官权力上涨,在服饰上也有所反映。魏忠贤名下的掌印、提督,均滥穿蟒袍,戴珍珠牌穗。魏忠贤外出时,戴束发冠,端阳节戴珍珠牌穗,穿的或者是用金线绣蟒龙的亵衣袄裤,或者是方补戎衣。衣服上的苍龙头角比藩王只少一爪,比御服仅是不用柘黄。又在禁地戴巾,穿亵衣,坐板径自抬出东、西华门。年轻的太监李永贞等亦都坐板。这时对宦官服饰、舆马方面的规定,也就无法贯彻执行了。
清代初年,宦官未入流品,也没有规定服饰。清代首任宫殿监林允升,是康熙的谙达,后人将他作为清代宦官之祖,称之为林老人,恩济庄宦官公墓的关帝庙内,供有他的像。从像中可见他戴的是高提梁红缨帽,所穿袍子虽已加上马蹄袖,但无蟒袍补褂。带子、靴子,仍然是明代的式样。后来才定制宦官服饰与外廷相同,新进无品秩的,冠皆无顶,待供奉勤谨出众时才能有顶。有官衔品级以后,帽上顶戴有鲜明的区别:二品是红顶,三品是正蓝顶,四品镍蓝顶,五品亮白顶,六品镍白顶,七品金顶,八品金顶带寿字。太监蟒袍前后所绣的禽鸟,亦有等级区别:二品仙鹤,三品凤凰,四品孔雀,五品鹭鸶,六品黄鹂,七、八品鹌鹑。那些无品级和顶戴的上差太监,穿紫色绸缎袍,前后补子上绣蟠龙花和五蝠捧寿。其他的都穿蓝色或紫色布袍,袍褂前后均无补子。清代对于顶戴很重视:进宫未满三十年的宦官,提为首领太监后,亦不得戴顶戴。据《清稗类钞》载,道光皇帝宠爱一个太监,给他娶了妻子,准住在南府中,但当他请求晋秩时,道光也只是特地创制了一种白玉顶戴给他,不敢乱了祖制。
宦官衣服的颜色亦有规定:春天是灰蓝色,夏天是茶驼色,秋冬是蓝灰色,诞辰穿绛紫色,忌辰穿青紫色。服装形式有靴、袍、帽、小褂、大褂、衬衫(无袖)、马褂、坎肩、叉裤、凉带、腿带等。其中除总管、首领可以穿马褂外,其他不论有无品级,均不准穿马褂,只能穿坎肩,至于赐李莲英黄龙马褂,则只是特例。大、小太监夏天都穿葛布、箭衣,系白玉钩,黑带。御前太监袖口均用白布缝制。所有太监靴子都是青色,但总管和首领穿的是长筒靴,其他只能穿角靴。
此外,还有一些更细的具体规定。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谕:下雨时,只准总管、首领、奏事太监、诗本太监、养心殿内首领小太监等戴红帽套,其余的均不得戴。若有违犯的,要立即将总管等治罪。咸丰二年(1852),文宗朱谕强调:“章服等级分别,所以辨上下,分贵贱也”,所以以后总管、首领等,非曾经赏过貂皮褂者,不准穿用;即正穿,亦不可至本色。貂帽除总管、奏事、首领太监、首领小太监可以戴用外,其余一律不准戴用。江山万代花样袍面,非赏过亦不准穿用。这谕旨除传谕各处总管、首领太监等知道执行外,还指明续修宫史时,要将之纂入,俾得永远遵行。
门禁制度
宫廷门禁历来都是森严的,宦官最早的、最重要的职掌之一,就是守御宫苑各门,防范出入。其后有关门禁的规定越来越严格。以明清为例,明代,洪武四年(1371),诏令立内城门禁之法:凡内官内使出入,皆用号牌,若有以兵器杂药到门者,按法律处置。洪武二十年(1387),命自今内官内使出差,不问有无文据,均由门官引奏,方准外出。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规定:小火者出皇城门,要比对铜符,若无铜符或不比对而放行,守门官军要治重罪。又有搜检制度:公差带金银缎匹外出,要凭勘合照验,写明往某处公干,所穿衣服的颜色、件数,回来时点对,若发现有不同,要即时奏闻 。后来,在《明律·兵律》中,又有“关防内使出入”条,规定:“凡内使监官并奉御内使,但遇出外,各门官须要收留本人在身关防牌面,于簿上印记姓名字号明白,附写前去某处干办,是何事务,由门官与守卫官军,搜检沿身,别无夹带,方许放出。回还一体搜检,给牌入内,以凭逐月稽考出外次数。但搜出应干杂药,就令自吃。若不服搜检者,杖一百,充军。若非奉旨,私将兵器带入皇城门内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入宫殿门内者,绞。门官及守卫官失于搜检者,与犯人同罪。”内官又不得私差在值校尉出外办事,长随内使李彦成,私差上值校尉孙三郎擅离信地,悬带铜牌,赍送内使宋堂告给顺天府优免户丁文书前去蓟州交割。结果孙三郎被押发陕西榆林卫充军,家小随住。李彦成被发南海子充净军种菜;宋堂则送司礼监奏请发落。由此可见,是以法律形式确保内使遵守门禁,维护宫中安全。即使是司礼掌印、秉笔,非奉公事亦不敢外出。万历时,王体乾提督礼仪房,奉差选奶口,也是寅出申回,不敢过夜。往北京沙河故里祭祀,也才住了一晚。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禁令虽然森严,可乘的疏漏仍难避免。据《明实录》载,景泰二年(1451),已有内监与白莲教徒交结,图谋不轨。成化十二年(1476),左少监宋亮等,甚至常把“妖人”李子龙引至万岁山观望 。成化十六年(1480),右监丞吴雄,将所得“妖书”带进宫内传播。万历以后,随着宦官势力的发展,门禁更为松弛,刘成竟把手执大梃的红封教徒张差带进了宫,企图刺杀太子 。而刚进宫不久的魏忠贤,竟“因囊乏,远赴四川见(税使丘)乘云为抽丰之计”,被丘乘云在北京的管家徐贵告到司礼掌印陈矩那里。但因为有内官监太监马谦的解救,魏并未受到什么惩治,徐贵后来反而被他害死。天启年间,魏忠贤更打着春秋二祭、看工、祭水等借口,一再远至涿州等地。这时的门禁制度对于权宦来说,已经是徒有虚名了。
为了维护宫中的安全和秩序,除门禁外,还有些相关的规定,如严禁在宫内争吵、打架。洪武五年(1372),定宦官禁令:凡内使于宫城内相漫骂,先发而理屈者,杖五十;后发而理直者,不坐。其不服本官钤束而抵骂者,杖六十。内使骂奉御者,杖六十。骂门官并监官者,杖七十。殴伤者加一等。内使等于宫城斗殴,先斗而理屈者,杖七十,殴伤者加一等;后应,理直而无伤者,笞五十。其不服本官钤束而殴之者,杖八十,殴伤加等。殴奉御者杖八十。殴门官、监官,杖一百,伤者加一等。其内使有心怀恶逆,出不道之言者,凌迟处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斩。首者赏银三百两 。《明律·刑律》又有“宫内忿争”条,规定:“凡于宫内忿争者,笞五十。声彻御在所,及相殴者,杖一百。折伤以上,加凡斗伤二等。殿内又递加一等。”即以法律维护宫内秩序。但事实上,这条例对权宦并无多大的约束力,在宦官势焰高时,尤其如此。熹宗继位不久,秉笔魏忠贤与乾清宫管事魏朝争与客氏对食,竟在乾清宫暖阁内乘醉相骂。时已夜半,把皇帝及司礼掌印太监等全都吵醒了,但熹宗不但不予惩治,反而给他们调停,把客氏归魏忠贤而勒令魏朝告病离开乾清宫。
清代,早在顺治十年(1653),上谕中已规定:“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其具体的出入查看腰牌、搜检等制度,则基本上沿袭明代。至于对宫中秩序的维持,清代极其强调惩罚,其情况详见下面有关部分。
奖惩制度
历代对宦官均有奖惩,但相对于其他制度来说,奖惩的随意性很大。奖励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蒙受恩宠,侍奉勤劳,或在帝位更易时有功,或在兼任职务上有所建树。奖励最常见的方式,除提升外,有赏赐房宅田土财物、赐名、赐爵、给免死券、致仕全俸、身后赐祭葬、赐谥、赠官,追赠先世、封妻荫子等。但各代亦有些不同,如东汉有使“侍御史持节监护丧事”;北魏有赐奴婢牛马,赐宫人;唐代有赐功臣号,为有功宦官绘图像于内侍省中,陪葬皇陵;宋时有为有功宦官特置殿使名“以宠之”,塑像或绘图像于太宗之侧,皇帝赐歌、赐诗、亲自写祭文;明代则加禄米,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祠额,立生祠,赐诗,赐字,赐宫内骑马、坐板等,荫及叔兄弟族人;清代有赏与主子同灶吃饭,赏穿黄马褂等。其具体事例,见于书中有关部分。这里只着重阐述惩处。
由秦汉至宋,见于各宦官传中的惩处,一般均有降职贬秩、削职、革爵、处死、抄家等,但其间亦有些差异。秦汉时有:受审坐牢,如“敕使(蔡伦)自至廷尉”。十常侍“乞自致洛阳诏狱”。降爵位,如具瑗被“贬为都乡侯”。收回分封给子弟的土地,如单超等“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减食邑,如黄龙等被“减租四分之一”。遣就国使其离开宫禁,如孙程等十九侯、黄龙等,或因触帝怒,或因罪发,被遣就国,即把他赶到封地。剥夺爵位,如侯览被“策收印绶”。革除官职驱逐出宫,如石显免官后,便得“与妻子徙归故郡”。徙边,如籍建等“坐徙朔方”。徒刑,《汉书·孝宣许皇后传》载,许广汉“坐论为鬼薪,输掖庭”,即在宫中服刑徒。抄家,如吕强被“收捕宗亲,没入财产”。处死,如中常侍樊丰、王甫、苏康等均被先后处死。
北魏时有:免为庶人,如段霸应处死,由于恭宗说情,被“免为庶人”;王遇被“夺其爵,收衣冠,以民还私第”。削职软禁,如苻承祖坐赃应死,由于以前曾得免死诏,所以从宽处理,“削职禁锢在家”。夺爵抄家,如刘腾死后,被“追夺爵位,发其冢,散露骸骨,没入财产”。处死灭族,如高宗即位,“诛(宗)爱、(贾)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唐代有:诏致仕,如杨复恭。有逐出京师,赶回老家或流放,如程元振被“削去官爵,放归田里”。高力士被“除籍,长流巫州”。田令孜被“削官爵,长流儋州”。用各种办法杀死,如鱼朝恩是在宫中被缢死;田令孜判缢死;刘希暹赐死;吐突承璀在宫中杀死;王守澄是送毒酒到他家(赐死);李辅国是使人刺杀;杨复恭是“枭首于市”;田务澄是被斩首、抄家。死后惩处的则有戮尸,如刘克明;削官爵、抄家,如仇士良;夷三族,如刘季述。
宋代有:赎金,如阎承翰“坐擅用群牧司钱,当赎金三十斤”。贬秩,如王中正“坐前败贬秩”,不久又再“贬秩两等”。降职安置外地或转外,如王继恩,“上恶其朋结,黜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籍没资产”。张继能,“坐罢内职,降授西京作坊使,出为邠宁钤辖”。削任外配,如石承庆,“坐削两任,配宿州”。杖配远州,如谭元吉等“协同妖妄,皆杖配远州”。张继能被“诏下御史府,免死,长流儋州”。死后追夺官爵,如杨戬,“诏追戬所赠官爵”。斩首,如“斩(周怀政)于城西普安寺”。身后枭首,如童贯在南雄被杀后,“函首赴阙,枭于都市”。削官、赐死、抄家,如李彦。
宦官传中所载的受惩处,多是因在宫廷斗争中失败,或有贻误军机、奸邪结党、过于贪酷暴虐等种种重大罪行,不惩处不足以震慑、清除对方势力或平息官军民愤怒。但除此之外,宦官触犯任何禁令,哪怕影响不大的,也要受到惩治,这点可以明、清两代为例予以说明。
明代永乐五年(1407),令司礼监榜示:今后内官内使,有言事不实及挟私枉人者,悉置重典。以后,对斋戒时“不谨”,随侍入坛时吐痰在地,与外戚、大臣联姻,寄私财于外人,擅入御茶房等不该去的地方,均分别给予惩罚。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司礼监掌印太监张诚之弟与武清侯李家联姻,于是张诚被降为奉御,发到孝陵司香,庄房田地均被没收。其弟侄等全部被革职判罪。对偷窃及在宫外经济犯罪,处分亦很严。宣德时,内使韦宗盗官铜造镀金器物,当时除交政府司法部门处置外,还命司礼监晓谕各监局,有盗官物及僭分者,事发处死;知而不检举,同罪。正统时,献陵神宫监少监阮菊伐陵树百余株私用,处斩。尚膳监内使王彰等盗用椒果杂物,被枷号在光禄寺前示众。成化时,内使杜衡盗内府金二两,银二百余两,被处斩。万历时,宫中失了一件珍珠袍,掌管内官王进等三人再四被拶鞫,结果打死;其余二人降做净军,其实袍子并不是他们偷的。宣德六年(1431),又令右都御史顾佐等晓谕中外:凡先所差内官内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内官内使寄顿财物,许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觉,与犯者同罪。自今内官内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军民人等,有投托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悉处死罪。这些都是为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但随着宦官权势的增长,这道晓谕很快便成了空文。宦官经济犯罪成灾,其情况见于下文经济部分。
对逃亡宦官的处罚,明初亦很重,六科廊职责之一,就是按月上报宦官逃亡的原因和数目。景泰五年(1454),内使田福逃亡到藁城县,被锦衣卫捕获,诏令立即处死。但后期稍有松弛,万历时,宫女吴赞女的菜户,因吴赞女移情别恋,愤而出家,得到同侪称许,亦未见对他有什么惩治。是否因当时宦官来源充足,供过于求,所以惩治不严,待考。
对内臣惩罚的方式,一般均是先拷打审讯,马房就是监官典簿奉旨问刑拷打内犯之处。明初,经审讯后的内犯,均送政府司法部门按律处理。如正统七年(1442),南京尚膳监内使郭敬失火,焚去所贮物料及房屋,被送司法部门,结案后,诏令立即斩首。景泰时,镇守内官陈海,用铁剑与女真人哈丹换马;司礼监高显强夺人房屋,均被司法部门审讯监禁。天顺时,太监牛玉被指在选皇后时作弊,被关到都察院监狱。但是,与此同时,皇帝和司礼监对刑审亦干预,如景泰时,内使阮绢依附司礼太监兴安,嘱管工的内官黎贤盗用官木,擅盖生坟佛寺。罪发,都察院判阮绢绞刑,并弹劾兴安。景泰帝偏爱兴安,“诏姑不问”,只把材料拆回便作罢。成化时,司设监沈绘不满情绪严重,奉御贾祥教他私造兵器以自防。罪发,司法部门根据《明律》判斩首,但他同党的二十一人却送司礼监奏请处置。
《弘治问刑条例》规定:内官、内使、小火者、阍者犯罪,请旨提问,与文职纳运炭米等项一例拟断。但受财枉法满贯者,不拟充军,皆奏请发落。嘉靖、万历的《问刑条例》亦一再重复申明,宦官犯罪之惩罚,与外廷同。但实际上,这时宦官犯罪,多由司礼监以“内批”的形式处理,轻者,降为奉御、私宅闲住,还是六品官;或者降奉御后,发南京新房闲住、发凤阳祖陵司香。重者,降小火者,发孝陵司香,这时已无官品。再重,则降充净军,发孝陵卫种菜。这时,南京守备大珰高坐堂上,喝“取职事来”,则净军要肩一粪桶并勺,趋过前而去。这种形式,虽司礼大珰得罪,亦不能免。种菜净军,昼夜只能住在菜圃,没有赦令,不能离开半步。更有严重的,则宣布夹四夹,拶四拶,打一百,发南海子长川打更,这就是表示要把他打死。
而更多的时候,是皇帝的随意处理,或皇帝、大珰对一般宦官任意处罚。如正德时,武宗先后将曾得宠于一时的大珰张锐、于经关到内书堂,令翰林官管束,每日从辰时到晚上,不准离馆。隆庆时,内官监李芳以进谏游乐得罪,穆宗先是勒令他闲住,接着又杖打八十,送刑部监狱待判。刑部尚书毛恺等,提出李芳罪状不明,无法判处。穆宗便以“事朕无礼”为由,令将他禁锢,后来终于贬到南京当净军。
神宗皇帝脾气暴躁,动辄责打宦官。这时,施刑的人害怕连累自己,常常加数重打;押解的人害怕连累自己,严加塾锁。据《酌中志》载,这时“受刑犯人得生者,十无一二”。即使宫人病死,有关内官亦要连带被责打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天启时,客氏之母遇一酒醉内官和她争道,魏忠贤便将夜行内官十多人逮捕,各狠打一顿,然后分别发往凤阳、南海子,有几个人竟因此死在了路上。
内犯还有被罚到更鼓房打更的,如天启元年(1621),魏忠贤害死王安后,便将他名下的曹化淳等发往更鼓房。更鼓房是个与牢狱差不多的地方,不仅工作劳苦,管理也很残酷。天启时,更鼓房牌子侯得用,对那些不行贿他的人,用连七纸写重病手本一件,藏在身上,叩见魏忠贤时便探听口气,如口气宽,便不呈手本;如可以将之弄死,则立即将手本呈上,称病故,然后回去将之弄死。三四年间,被他这样害死的内官,达百余人之多。
就是对内书堂的学生和那些小宦官,处罚也很重。凡背书、写字成绩不好,或损坏书本,犯学规的,由词林老师批个数目,交提督责罚处理。其余小事,轻的,由学长用戒尺打手;重的,在圣人前罚跪;再重,则扳着几炷香,即向圣人直立弯腰,用两手扳住两脚,或半炷香,或一炷香,以致犯者头晕目眩,甚至呕吐、昏倒成疾。
以上所述对宦官之惩罚,基本上是对一般犯罪、违法乱纪而言,若一旦被认为所犯之罪是危及皇权,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刘瑾,被判降奉御、发往凤阳后,武宗还令给他故衣百件。但在抄他家,发现大量违禁品,尤其是常用的扇中藏有利刃时,“始大怒,曰:‘奴果反。’趣赴狱”。结果是“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刘瑾这磔刑,是俗语说的千刀万剐,碎尸万段。即用三天时间,每天按一定数量,向他身上共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把肉以小指甲般大小割下来,直至死去,才开膛、砍头 。明代这种刑法的残酷,又在历代之上。魏忠贤上吊死后,仍下诏磔其尸,悬首河间,抄家灭族。
清代历帝,对于明代宦官擅权乱政的教训极为重视。顺治元年(1644),即谕令“朝贺大典,内监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礼”。顺治十年(1653),上谕:“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并将此谕用满汉两种文字刊刻,告示亲王以下全国臣民。两年以后,又仿照明太祖的办法,命工部铸铁牌,立于内务府和宫中交泰殿内,上书“倘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康熙借顺治遗诏,指斥“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乾隆在编写《国朝宫史》的上谕中,亦说:“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寺。”因此,清代对宦官的管理非常严格。如道光时,进宫未满三十年,或曾受过处分发往外地放回的,均不得挑补为宫内、圆明园首领太监。即使因缺额而提前挑补,也只能食首领钱粮,不得戴用顶戴。咸丰时,又令凡挑放八品首领官职未满三十年的,不准支食四两钱粮,只有皇帝特旨简放的才例外。从敬事房有关的档案中,可见这情况直到光绪末年,仍无多大变化。又如太监犯法,其上级主管人员,亦层层分别从严惩处,等等。
清初,针对太监种种过犯情况,先后分别制定了各种治罪条例或章程,后来在制定《宫中现行则例》时,又把它们综合为处分条例,对各种处分作了具体的规定,明确凡宫殿监等处太监,在宫外犯法的,由外部奏明,按《清律》治罪;在宫内犯法的,如情罪较重,宫殿监不敢擅专或不敢剖断,则具牌奏明,交由内务府治罪或审理,重者交总管内务府,轻者由总管和各处首领太监责罚。
敬事房和太后、皇后、嫔妃宫中的散差,是管宫中责罚的。散差有掌刑太监多名,他们随身背着用黄布袋装着的行刑用的杖和板。杖和板都用煮过的竹子制成,杖是长五尺圆五分的实心竹,板是长五尺、宽五分的毛板竹。行刑分殿上行刑和处所行刑两种,殿上行刑由主子监视,打轻了要反坐;在处所行刑则可以设法得到轻打。行刑时,先将受刑者按倒在地,令撅起臀部,然后一人按头,两人按手,两人按腿,一人掌刑,一人喊数。掌刑者要注意打得皮开肉绽,但不准伤骨头。受刑者一面挨打,一面口里要求饶,若不求饶,则视为顽抗,要加倍处罚,甚至打死。行刑后,由两个人架着受刑者到主子那里叩头谢恩,行刑才算结束。
慎刑司是内务府属下处罚太监的机构,如乾隆十九年(1754),翊坤宫东配殿失火,负责打扫和看守的首领太监王世臣、徐朝相,便被交到慎刑司治罪。光绪末年,慎刑司增加了“气毙”之刑,即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者口鼻耳封闭,再用杖责打至死。戊戌变法后,慈禧就是用这种刑罚,将光绪宫中那些给维新派报信的太监弄死的。
太监的处分则例,分“宫殿监处分则例”和“各处首领太监等处分则例”两项。
“宫殿监处分则例”分三等罪,共十二条。规定对凡禁约之事日久废弛,奏事不敬或错误,办事拖延,升、调、补和处理各处首领、太监不公,遇事推诿,对犯罪检查不力或不按例办理,浪费钱粮、失仪,非因公使令各处首领太监,等等,都要分别罚不同数量的月银,并记录在档;最重的,直到请旨革职、降级。若屡犯不改,则由宫殿监具牌请旨,交总管内务府治罪。若互相隐瞒包庇,则将众宫殿监等,俱交总管内务府从重治罪。
“各处首领太监等处分则例”亦分三等罪,共十五条。凡有口角斗殴,白日酗酒,不慎火烛,不勤慎坐更,喧哗无礼,收储钱粮器物遗失或损坏,将内外事情妄行传宣,不服管辖,失误关防,擅至不该至之处,告假超时回宫,祭祀时献器物不敬谨,传集不到,等等,都要分别受到罚月银、责打的处分,并记录在档。若屡犯不改,宫殿监具牌请旨,交总管内务府治罪。总管内务府治罪条例多达五十余条,包括内容很广泛,处罚也很严厉,如:在宫中私藏鸟枪、火药、金刃器械,大太监擅自责打小太监和宫女,均立即正法。无故持刃入殿或醉酒胡闹者,在宫内自缢被救活者,均处绞刑监候。用金刃自伤者,立即斩首。在园庭自缢被救活者,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自缢死者,其亲属发往伊犁或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请假或公差外出超时回宫,外出喝酒、听戏,容留外人在他坦(住处),有病外治愈后不禀明回宫服役,偷钓庭园鱼虾,与王公大臣交往,越诉,皇帝召见大臣时擅自进殿,将洋药带入宫,随驾外出后不一同进宫,赌博,抽鸦片,逃跑,等等,均要分别受到扣月银、枷号、杖责、发往边远铡草或为奴等处分,直到处死。
这些处分,一般都规定得相当具体,如关于禁止吸烟,所有太监、首领等,在下旨后三个月内,要将烟具交出,保证以后不再吸。否则,在宫殿值房、禁门以内各值房吸的,系太监,则判绞刑,奏明后交刑部监禁,并执家属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失察之总管革职;该处首领发黑龙江给官员为奴;同屋太监均发往打牲乌拉给官员为奴。如系首领吸食,将失察之本管总管奏请革职发遣;该处其余首领及太监等,俱发吴甸铡草五年;贩烟之太监与吸者同罪。在外围值房各他坦公所吸食者,该太监枷号六个月,满日,发极边烟瘴永远枷号,交地方官转饬看管,遇赦不赦;失察之总管奏请实降二级;首领革职;同屋太监发吴甸铡草三年。如系首领吸食,均照禁门以内新拟罪名办理。如有告假在外,或潜往私宅,或在他处吸食,该首领太监在慎刑司永远枷号不赦。若系在该首领太监私宅,将其家属杖一百,徒三年,房屋入官。如系他处,将容隐之人交刑部加等治罪,亦将房屋入官。陵寝当差首领太监吸食,即行奏明,解交慎刑司严审,照在外围吸食一样处理。王公门上之首领太监及大臣宅中太监吸食,奏交内务府审实,在慎刑司永远枷号不赦。如半年以后在宫内吸食者,判斩监候。在外围等处、陵寝当差者,王公门上、大臣宅中,已为民太监等,若有吸食,判绞监候。其有关人员失察,仍照前办理。
从清宫档案《内务府奏销档》中,可以见到清代太监因违犯各种条例而受到惩处的人不少。如:乾隆年间,饭房太监王国泰持刀刎颈,被发瓮山铡草十五年。御膳房太监马凤因衣服不齐,怕总管责打,自刎,被发瓮山永远铡草。静宜园太监赵世贵自缢死,该处总管首领不立即禀报,被交宫殿监督领侍查办。钟粹宫太监王凤来,偷貂皮等物后逃走,被获,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马玉偷银器典当,被获,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所用去的钱,由家产严追解交回。坤宁宫太监马升,偷数珠等逃走后,自行投回,发打牲乌拉充苦役。圆明园太监因观音庵失火,发打牲乌拉充苦役;副首领孙国用失于查管,交总管内务府治罪。太监李连栋放火盗窃,被正法;父母及三个弟弟共五口人,全被发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副首领尹玉凤失于稽查,太监王凤不报,逃避躲匿,均发黑龙江。赵国宝与宫女五妞相好后变心,致五妞越墙到他处自刎,赵被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蔡勋进上御葛布袍袖有针,被枷号一个月,鞭一百,枷满后充当苦差;其首领太监被革退首领,鞭一百,仍令当差;六品总管太监马国用降七品,罚一年钱粮。咸丰六年(1856),太监丁得禄在外廷吸食鸦片,有关人员分别受到罚月银几个月至两年;有的还被革去顶戴。
对太监的处分,有时皇帝亦亲自处理,或由有关大臣联名上奏有关处理情况,这些在奏销档中亦有反映,如:乾隆十八年(1753)四月二十七日,圆明园太监王凤逃走,被获,“奉旨,王凤着发给铡草。钦此”。苏成,系静宜园太监,因本处陈设被盗,于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三十日奉旨:“苏成着发往铡草,钦此。”御书房太监朱祥,因误了差使,怕首领责打,外躲,但无处藏身,便剪去发辫,易名李芳,投在万善殿当和尚。后被挑补到畅春园内佛堂当差,被番役拿获。总管内务府根据初次逃走太监,拿获者交吴甸铡草一年的圣旨,以及《清律》载:凡僧道私自簪剃者,杖八十,并还俗;凡二罪以上交发,以重者论的规定,拟将朱祥先发吴甸铡草一年,然后鞭八十,勒令还俗,再交总管太监料理。为此,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太保大学士、议政大臣傅恒、大学士、议政大臣来保、内务府大臣海望一同具衔上奏,以见其对处理之慎重。
被发铡草的太监很多,铡草处看守严密,如吴甸,铡草太监的住房,外围墙两层,高一丈;内围墙高五尺余。铡草太监日间进圈,由厩长等看守,晚间关禁后,交与特派看守领催、披甲人等看守。如有逃亡,有关人员均要受到处分。如尹进忠逃走后,除严讯所有人外,派番役到他原籍霸州缉拿;厩长福秀、副厩长绥哈芬,分别以失察受到处分。
对太监的请假,掌握很严,《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太监等遇有祖父母及亲丧事故者,可以按照品级高低,分别得到长短不同的假期。嘉庆十八年(1813),明确规定,凡太监请假,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派官役前往其门首稽查,俟其假满进宫,再将官役撤回。这是为了防止太监逃走。
不仅宫内,就是在宫外,对太监的管理惩治也比较严厉。《则例》规定:太监随围在外与地方人等不准稍有交涉,“倘再有滋扰不法之处,一经查出,即行正法。”“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骂人父母”,否则许被骂之人即行重责。遇亲丧事故请假回家的太监,不许向官员兵丁民人等无故攒收份金,等等。清帝对在外违法乱纪太监的惩治,比较重视,据《内务府奏销档》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有内监僧人在外戏侮巡检,咆哮公堂,被发往黑龙江安插,总管事务之海保、富贵,回护太监的千总,均分别受到了惩处。乾隆帝公开声称:“朕岂曲庇内监之主,嗣后太监有在外漫骂生事者,听人责惩,朕皆不问”,所以官员对太监比较敢于管辖惩治。
据《清稗类钞》载:康熙帝南巡,所经之处,督抚派人清道,御道居中,禁人行走。某典史巡到某处时,圣驾未至,有太监戴孔雀翎,昂然直驰御道,典史劝阻反遭到呵斥。典史命把他拽下马,押到官栅,坐堂执法,直打到他叩头哀求才罢。督抚大惊,具奏,自请处分,让典史在宫门外等待发落。结果,康熙以典史敢管太监,把他升为四品官。雍正帝有事先陵,经过知县孙诏成境内,刚好下大雪,行宫门外积雪数寸。按惯例,宫门内外扫雪等事,由宫监负责,但宫监因在当地勒索不遂,大发脾气,把县官呼来扫雪。孙诏成一面扫雪,一面对他说:县官为天子扫雪,不是羞耻的事。宫监大怒,要聚众揍他。于是孙诏成知道了谁是魁首,立即命皂隶把他捆绑杖打。世宗知道后,高兴地说:“这知县好大胆,太监滋事不可赦”,着交所司治罪,并召见孙。不久,提升他直到两浙盐运使。高宗幸滦州,某随侍太监滋扰民间,热河巡检张瀛苦劝之不止,呼役缚他杖打,因此受到弹劾。高宗却“甚嘉之”,特旨令越七阶提升他为同知,而将太监遣戍。
类似情况,在以后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道光十六年(1836)九月的邸钞,有一则记:提督恣送轿夫葛三等赌博一案。此案,总管太监张尔汉因太监张进忠赌博被获,辄向步军统领私行恳求,将张进忠放出,实属曲法嘱托。若仅照嘱托公事拟笞,殊觉轻纵。张尔汉应比照监临势要曲法为人嘱托律,拟杖一百,业经革去总管,应勿庸议……恭俟命下,移咨内务府,照例办理 [13]。可见即使是总管太监,在外违犯条例,也不轻饶。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处死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慈禧容纵六品蓝翎太监安德海到广东,经山东时,被巡抚丁宝桢劾奏,同时加以逮捕。
尽管安德海非常嚣张,一口一个奉太后委派,丁宝桢还是不待圣旨下来便把他杀了,并暴尸三天。朝中,慈安太后接到奏疏,征询亲王及军机大臣意见时,他们一致认为“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请令就地诛之”[14]。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其他一些矛盾,但在不能容纵太监上,是比较一致的。八国联军进京,慈禧逃往西安,甘肃藩台岑春煊受命整肃军纪,见有骑驴的太监,不请旨便把他杀了,因为驴显然是夺自民间。对此,李莲英虽然不满,慈禧却并未置意 [15]。
不过,尽管有这些事例,也不能忽视一点,即从总的来说,清代对太监的管理惩治,也是日久弊生,漏洞潜滋暗长,乾隆五十二年(1787),已有谕旨指斥太监把坤宁宫祀神后应给散秩大臣、侍卫吃的肥肉偷走 [16]。嘉庆时亦有谕旨指责门禁废弛,闲杂人等任意进入宫禁,并终于发生了林清等二百余人冲进宫中的变乱。清末,随着政治的腐败,大小太监的违法犯纪已经成风,李莲英、小德张干预政治,交结朝臣、接受贿赂,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容纵庇护;小太监也可以大闹街头,砍伤兵勇仍然逍遥法外。这时,各种则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具文。
婚娶、养子制度
宦官之婚娶,未见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历代对此均已认可。情况已见第二章,此处不加赘述。养子制度则散记于历代史籍,从中可知自汉代以来,历代宦官有养子的不少,而且均有法制上的保证,有时也有一些限制。汉代,安帝时,鄛乡侯郑众养子闳承嗣袭爵,开了养子袭爵的先例。顺帝时,明确规定宦官可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但“不得为牧人职,不得吏察孝廉、列身豪族名士”。北魏宦官养子可以出任官职,刘腾两个养子分别是郡守、尚书郎。而唐代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唐初,不许宦官养子,但这禁令并未得到贯彻,杨思勗、高力士等都是宦官养子。《唐会要》载,德宗时,定内侍省五品以上,准养一子,但要是同姓的,而且初养日不得过十岁。不过这规定亦未得到贯彻执行,不少宦官养子数目大大超过了一人。仇士良有五子,杨复光有数十,杨复恭有六百。这众多的养子,自然多不是同姓,也不会都是小于十岁。恰恰相反,过去养子是为了承嗣,求得自己亦“有后”的心理安慰,所以养子多有年幼的。而唐代中期以后,养子作用的重点,已在于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这时先是通过荫庇、承嗣、强请等方式,使养子成为外廷的高官、内廷的高品,鱼朝恩五个养子中,年长的四人,一个封公,食邑一千五百户;三个是内侍省高品。以后更着眼于使养子掌兵权,因而选为养子的对象,已是“慓士奇材”,而绝不是同姓幼儿。田令孜由于与杨复光有矛盾,“以复光故,才授诸卫将军,皆养为子”。杨复光儿子用守字排行,有三个是节度使,一个是防御使,“其余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杨复恭“以诸子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以致“天下威势举归其门”,“广树不逞皆姓杨”。养子已成了扩展势力,把持兵权,交结藩镇的重要手段。唐代养子制度对宦官专权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各代所远不及的。唐末,昭宗下令宦官“不得养子”,以图裁抑宦官势力,但未及执行,唐已覆亡了。
宋代吸取了唐的教训,从太祖起,屡次严禁私养宦者,先后规定内侍年三十以上,方许养一子;士庶敢有阉童男者,不赦。自今满三十,无养父者,始听养子,并要到宣徽院记名;入内供奉官以下,养次子为内侍者,斩。但宦官养子亦不少,而且是补充宦官缺额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情况亦已见于上文。明代大宦官亦有养子,如曹吉祥嗣子曹钦(因曹吉祥助英宗复辟有功,封昭武伯),刘永诚嗣子刘聚等,但远不如唐、宋之普遍,对当时影响不大。清代,李莲英、小德张都以侄子为养子,但那仅是为了承嗣继产,而且不久清政权就结束了。
升迁制度
宦官之升迁,弹性很大,何时、何种情况升迁,升迁的幅度,均没有严格的制度,往往决取于受恩宠的程度。即使在有《磨勘法》规定“内侍都知押班,须年五十以上,历任无赃私罪者,才能担任”的宋代,有司礼监专职负责的明代,也是如此。清代,挑补首领太监,必须是进宫满三十年以上的,但后来亦已松弛,李莲英十八岁便当上了首领太监。
宦官的升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品秩、职位的提高,一是岗位的调动。前者比较明显,无须赘述;后者则包含比较广泛,历代名式有些不同。汉代,由宫廷杂职迁内廷各官署的令、丞。唐、宋代,从省下属机构转入省;从内侍省转入内内侍省。明代,从其他监局转司礼监。清代,从外围转入内围;从热火处等转为内廷太监等。只要向帝王靠近一步,都可视作升迁。接受差遣、兼职增多,亦即职掌扩大、职权增加,更为得到信用,亦可理解为升迁。如秦、汉时,中常侍兼领大长秋,或中常侍兼领内廷各官署令(由于中常侍品秩高于令,故这种兼任称“加位”,中常侍蔡伦即曾“加位尚方令”)。唐时的充任使职,如仇士良“以本官充平卢军监军使”。宋时的诸司使,如皇城使、内客省使。明代的监军、镇守等。清代的加品顶戴,亦属升迁,但这种形式极少出现。
休沐、致仕制度
宦官的休沐、致仕制度,均未见于史籍,但从各宦官传和有关史籍的零星记载,可以知道它们都是存在的。以休沐而言,首先,历代宦官虽然供职内廷,但权宦在宫外都有豪华的私宅,多数还娶妻养子,自然只有休沐日,他们才能回去一享天伦之乐。其次,若干传记中,均写到传主休沐的情况,如蔡伦“每到休沐,辄闭门绝宾”;高力士“虽洗沐未尝出,眠息殿帷中”。其他史籍亦有有关情况,《酌中志》载:王进德“每休沐之暇,即合户焚香,闭门读书”;清《内务府奏销档》载,祭神房罗思贵每月送钱粮回家,而别的太监亦有在这时来串门的。所以,说这时有休沐,大致不会有错。
以致仕而言,唐代严遵美是“求致仕”离宫的。梁从谦致仕仍保有全俸。宋代宦官致仕时可以带职,甚至升迁一官,如刘承规,原系景福殿使、新州观察使,因病求退,得以检校太傅、左骁卫上将军、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致仕。致仕后还可以“落致仕”,即再起用,如张去为致仕后,又“诏落致仕”,委任为提举德寿宫、特迁安庆军承宣使。致仕可以是自己请求,如刘承规;也可以是强制的,如张去为就是“令致仕”。请求致仕也可以不予批准,如关礼“乞致仕,不许”。明代宦官传中未见载及致仕事,但《明武宗实录》中,载有太监刘瑯致仕,可见致仕也有,但不多。清代李莲英、小德张等以原职级并领取赏赐出宫,亦当是致仕。而下层太监的出宫则明确为“为民”。
全部回复

评论区开荒,我辈义不容辞
来抢第一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