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打开APP
从J联赛的发展看中国足球到底该不该限薪
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将出台更严厉的限薪令,本土球员顶薪将不得超过500万人民币。一时间,关于降薪的争议再度甚嚣尘上,一方面支持者认为限薪有利于消除泡沫,保证联赛健康运营;而另一方面反对者认为限薪会降低联赛的精彩程度,并且还会严重影响国内的足球热情。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日本球员之所以能留洋遍地开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J联赛的工资较低,球员不得不到海外打拼。所以,因此我们就应该支持足协的限薪政策了吗?显然不能简单粗暴地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到底如何看待限薪?这是中国足球希望的起点,还是中国足球将迎来寒冬?本期《日本足球密码》,让我们先来看看J联赛是如何从金元时代走上安定经营的道路,再回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初期的J联赛热潮】
1993年5月15日,谋划已久的日本足球职业联赛终于开幕了,足球在日本这个国度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
在最初的赛季中,除了清水心跳以外,其他球队基本上都是从之前的企业足球部转变而来。比如丰田汽车变成了名古屋鲸八,住友金属变成了鹿岛鹿角,横滨水手和横滨飞翼的前身分别是日产汽车和全日空,松下电器改名为大阪钢巴,东洋工业则变成了广岛三箭。
而两家强势的俱乐部甚至还首个赛季中保留了企业的名称,读卖新闻在1994年才更名为川崎绿茵,而三菱重工到1996年才更名为浦和红钻。
由于最初联赛球队数量较少,为了增加比赛场次,提高观赏度,联赛被分为两个赛段进行,也就是说每两支球队相互之间都要踢四场比赛。赛程密度让球员苦不堪言,而在1995赛季,球员们甚至经历了长达7个月的一周双赛。
这还不是普通的一周双赛,因为日本人还在J联赛中加入了一项奇葩的规则。1993年至1998年,J联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平局的联赛,是的,联赛打平必须打加时,加时赛采取金球制,而平局最终需要点球决出胜负。
联赛最初是没有积分的,按胜场多少排名,而后期积分制引入之后,90分钟获胜积3分,加时赛获胜积2分,点球获胜积1分,输球积零分。
这便是最初的J联赛,尽管我们目前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联赛显得并不是那么职业。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各大企业都纷纷砸钱,认为足球是一个拓展企业影响力的好项目。
为了争夺冠军,各支球队不惜花重金引入高水平外援。济科、邓加、贝贝托、利特巴尔斯基,斯托伊科维奇,甚至还有马拉多纳,众多世界级球星都出现90年代的日本赛场。
大量的外援进入这也导致在那个时期,除了三浦知良等球员以外,各队的日本球员都基本处于陪踢的状态。无论从战术上还是实力上,各支球队都高度依赖外援的发挥。
【J联赛繁荣之下的危机】
尽管这是个烧钱的游戏,但日本的企业却前赴后继地冲了进来。从1993年首个赛季的10支球员,到1996年已经迅速扩军到16支球队,并且决定开始考虑组建次级联赛J2。
然而,J联赛在一片表面的光鲜繁荣之下,实则面临诸多问题。
一是本身棒球在日本的影响就根深蒂固,在经历了初期的新奇体验之后,人们发现还是看棒球更有意思。二是,球队扩充太快,而辐射的地区较为集中,有限的球迷群体被不断地分流。于是,J联赛火爆的球市逐渐冷清,观众越来越少,到90年代末场均人数甚至不到一万人。
而就在J联赛关注度日益降低的时候,1997年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来了。
先是鸟栖F俱乐部因为股东陷入巨额赤字,没有了经济来源的他们被迫宣布解散。同年,清水心跳因为静冈电视台宣布撤资,一度面临解散,最后靠着当地企业和市民的募捐才勉强保留下来。
当然,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还是横滨飞翼合并事件。同样是因为球队股东方的撤资,横滨飞翼面临存亡危机。而在广大球迷不知情的情况下,横滨飞翼和横滨水手宣布合并,改名为横滨F水手(横浜F・マリノス),而“F”正是“飞翼(Flügels)”的开头字母,也是横滨飞翼留下的唯一痕迹。
【J联赛的安定经营之路】
显然J联赛不能再这样毫无节制的扩张下去,如果不及时出台相应政策,只会有越来越多的球队消失。当时的J联盟主席川源三郎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方面,一些措施甚至沿用至今,以保证J联赛走上安定经营的道路。
比如,要求俱乐部股东多样化,以免单独持股方撤资后,球队完全没有资金来源。又比如,要求各家俱乐部经营透明化,俱乐部财政收入与支出情况都必须公开,以便外界随时了解俱乐部的经营状况。
于是,各俱乐部为了达到J联盟的规定,不得量入为出,走上可持续的经营道路,而这条发展道路上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便是开源与节流。
在比赛日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各支球队大力挖掘赞助商。为什么J联赛的球衣都比较难看,看看他们球衣上赞助商的广告位便知道。
除了收入的增长,保证俱乐部健康运营最重要的一环,便是控制支出,而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最大的支出便是球员工资。虽然近年来,J联赛的球员的平均工资逐年上涨,但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2020年平均年薪为3446万日元(约217万人民币)。
在J联赛中,大概有三种合同类型。第一类A合同,没有年薪限制,每家俱乐部最多可与25名球员签署此类合同。第二类B合同,没有人数限制,最高年薪480万日元。第三类C合同为新人合同,上限同样为480万日元,如果新球员没有达成规定的出场时间,3年以内都可以签署C合同。
可以看出,J联赛实际上并未对球员年薪有太多的限制,如果俱乐部自己需要,都可以签署没有上限的A类合同。但是,各家俱乐部为了收支平衡,在总体不能运营不得连续三年亏损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严格控球员工资支出。
现在我们在回过头来讨论中国足球是否该限薪?
显然,对于职业生涯并不太长的球员来说,在一个行业里做到全国的顶级水平,谋求一份高薪并不过分。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超球员的工资确实太高了。可是,球员工资高是根本的问题吗?
并不是,中国足球的问题在于100天内22家俱乐部消失了。比起顶层球员工资高的问题,底层俱乐部解散,球员欠薪的问题显然要更重要得多。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让更多的俱乐部健康运营下去,让更多的球员有球可踢。
而现在的政策来看,限薪本应是一种手段,现在变成了一种目的。简单粗暴的限薪也许会为中国足球降温,但对中超关注度的影响也是毁灭性的。J联赛不限薪,却能有着大批低薪的球员同时,还能拥有托雷斯、伊涅斯塔这样的门面提升关注度,提高联赛价值。
无论如何,我们将再次见证历史,中国足球最疯狂的金元时代即将成为过去,希望在最后时刻中超球队再拿一次亚冠冠军吧。
下期预告:J联赛的创办与改革,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人物,川渊三郎,一个在日本足坛几乎被神话的名字。一位棒球少年是如何进入足球国家队?一位古河电工的营业部长又是如何成为J联赛掌门人的?下期《日本足球密码》将为大家带来川渊三郎的故事,欢迎各位JRs关注,谢谢。
阅读 444922
这些回复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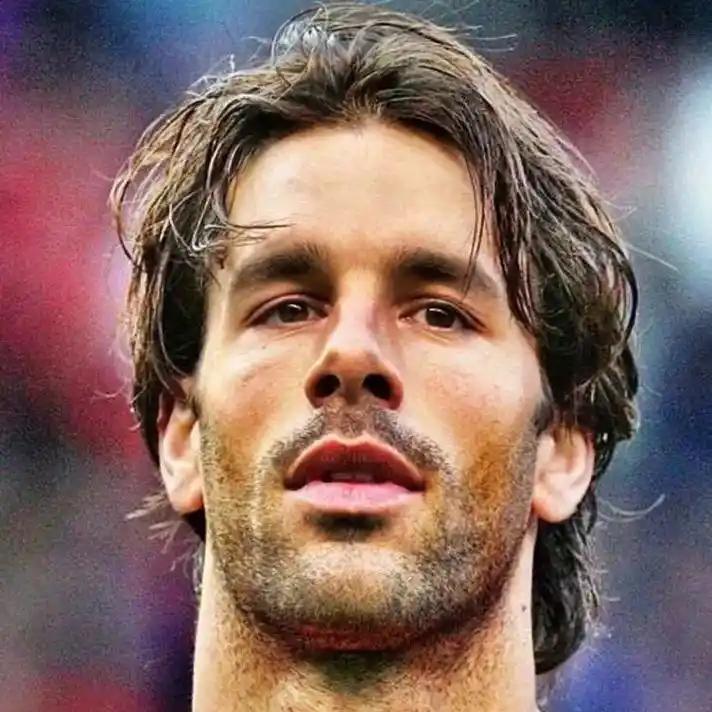
曼联主教练范尼
· 上海既然开放归化了 那限薪是可以的 能者居之
亮了(333)
查看回复(3)
回复

最后的四合院
· 北京个人观点,你踢得不行还年薪好几百万?俱乐部就不给你那么高年薪。但是不应该这种强制限薪。
亮了(239)
查看回复(7)
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