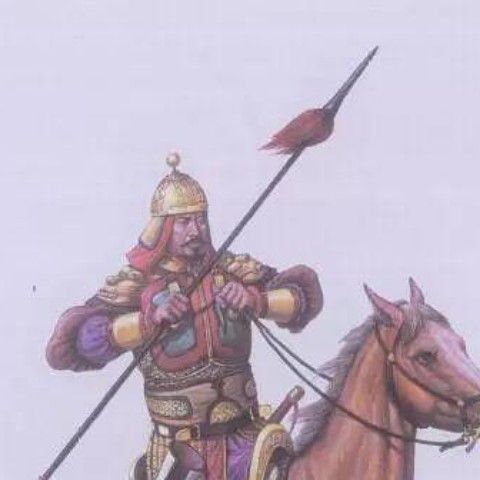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从归义军的内乱到西汉金山国的建立(文录摘自于《战争事典》)
文德元年十月十五日,朝廷终于派遣宋光廷为使节押送旌节前往沙州。随着朝廷使节的车驾缓缓进入沙州城,张淮深终于得到了盼望了20年之久的节度使旌节。面对旌节,他在喜悦之余却难掩失望,喜的是终于获得了朝廷的认可,失望的是此次朝廷授予他的职务仅仅是沙州节度使、沙州观察处置使。遥想当年,他的伯父张议潮作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十一州观察使,是何等威风。即使是咸通四年朝廷析置河西,分置瓜沙、凉州二节度使,归义军的观察范围仍有九州。现如今,节度使旌节虽到,但自己的势力范围却被压缩至沙州一地,连毗邻的瓜州也被朝廷剥离,权柄被大大削弱,他又如何压制境内窥伺的豪宗大族,以及张氏家族内部的觊觎者?
果不其然,大顺元年(890年)二月二十二日,沙州城内突然发生政变,乱军杀向军府,张淮深猝不及防,与夫人陈氏及其六子——张延晖、张延礼、张延寿、张延锷、张延信、张延武等人同日遇难。这一年,张淮深59岁。张淮深究竟为谁所杀,史书上没有留下明文记载,但其墓志铭给后人留下了这样的线索:“哀哉运蹙,蹶必有时。言念君子,政不遇期。竖牛作孽,君王见欺。殒不以道,天胡鉴知?”
根据《左传》的记载,所谓“竖牛”乃是指鲁国公卿叔孙豹与庚宗妇人私生的庶长子,此人长大后投奔其父,叔孙豹平时常叫他为“牛”,又让他担任了“竖”这样的小官,故曰竖牛。竖牛为人机警颖悟,很得叔孙豹的喜爱,因此常被委以重任,掌握了不小的权柄。后来,叔孙豹病重,竖牛认为篡夺叔孙家权力的时机已到,先杀害了他同父异母的两位弟弟孟丙、仲壬,又隔绝内外,饿死了他的父亲叔孙豹,随后立另一同父异母兄弟叔孙婼为嗣,是为叔孙昭子。不料,叔孙婼并不是甘于受人摆布的傀儡,而是颇有心机手段的厉害人物,在次年地位稳固后,便要以祸乱叔孙氏的罪名诛杀竖牛,竖牛只得连忙逃往齐国,后被孟丙、仲壬两人之子所杀。
墓志铭的作者使用这样一个典故,便是要委婉说明是张淮深的庶子杀害了张淮深夫妻以及同父异母的兄弟。后人根据敦煌文献中的一些蛛丝马迹,推测是张淮深的庶子张延思、张延嗣两人动手发动了政变。嫡庶有别,待遇势必不会一样,父子兄弟间因此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被有心人利用,在他人煽动下,两名庶子铤而走险,用流血政变一洗心中积怨。幕后策划者应该就是张淮深的堂弟张淮鼎。张淮鼎回到沙州后,很快便凭借他父亲张议潮在归义军的崇高威望拉拢了许多实权人物,成为张淮深统治的最大威胁。最后,也正是他利用人心的贪婪与怨毒,成功夺回了他父亲失去的权柄。至于张延思、张延嗣两人,自然也是如同竖牛那样,被新的上位者找借口除掉了,这样既可消除潜在的威胁,又撇清了自己与政变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张淮鼎执掌归义军大权后,自称节度留后,并派遣使者入京请节。朝廷或许是掌握了归义军政变的实情,或许是要继续打压归义军,并未赐下旌节。而仅仅两年后,张淮鼎就去世了,归义军政权被归义军另一实力派人物——瓜州刺史索勋夺取。
索勋出身的索氏家族也是沙州的名门望族,家境豪富,与其他沙州大族多有联姻,势力盘根错节。索勋的曾祖父索稚之妻便是曾任归义军瓜州刺史的阎英达的姑姑。阎氏也是沙州的古老大姓,当年率领沙州军民抵抗吐蕃入侵十余年的阎朝便出自该家族。也正是凭借这一点,索氏家族成员在吐蕃人统治期间曾出任汉人所能当上的最高官职——都督。索勋的父亲索琪也是张议潮策划的沙州起义的重要参与者,并在归义军前期的政局中十分活跃,担任要职,在归义军政权中的排名尚在阎英达之前。
索勋成年后,文武兼备,才华出众,张议潮对这位年轻人青眼有加,十分赏识,不久后即将其招作东床快婿。索勋后来继承父业,“一从旌旆,十载征途”,在归义军与周边势力的历次战斗中屡立功勋,曾参与过张淮深再次收复凉州的战役,也因此于乾符六年出任瓜州刺史,成为归义军内的重要人物。索勋在瓜州主政十余年,在军政、经济、文化方面都颇有建树,在当地很得人心,积蓄了强大实力。在大顺元年的那场政变中,他作为张淮鼎的堂姐夫,应该也出力不少,在政变后得以继续担任瓜州刺史一职。张淮鼎去世后,其子张承奉年幼,张淮深一系在之前的政变中被清除殆尽,张氏家族中已无杰出人物,张议潮的几个女婿中,肃州刺史阴文通和凉州司马李明振也都已经去世,索勋既是张氏懿亲中唯一健在的长辈,又出自沙州本地的传统大族,更是归义军中的实力派,他凭借这些优势一举夺取了张氏家族的权柄,成了归义军新的统治者。
朝廷对索勋取代统治归义军将近半个世纪的张氏家族一事,应该是持乐见其成态度的。张淮深为获节度使旌节,屡次遣使请节,先后花了近20年时间,而索勋刚刚上台便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不久后即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等使,不但重建了归义军的军号,还恢复了对瓜、伊、西三州的观察权。
顺利获得朝廷旌节,无疑让索勋颇有些志得意满,放松了对其他势力,特别是张氏家族及其姻亲家族的警惕。张氏家族虽然人才凋零,但毕竟执掌权柄数十年,依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索氏家族的大权独揽又让沙州其他大族心存不满,一场新的政变很快便在密室中开始策划,其主谋便是李明振之妻、南阳郡君张氏,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张议潮的第十四女。李明振所在的李氏家族也是沙州大族,族望甚高,他们一向称自己是西凉政权的建立者——凉武昭王李暠之后,与大唐皇室亦有亲属关系,在当地很有实力,张议潮将女儿嫁给李明振,便有拉拢该家族之意。李明振兄弟四人,其中三人在归义军出任要职,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李明达为河西节度衙推兼监察御史,李明得为沙州录事参军。索勋主政时,李明振已经去世,张氏为李氏家族的实际当家人。
乾宁元年(894年)九十月间,张氏在联络沙州城内对索勋不满的各方势力后,带领她的四个儿子突然发动政变,杀死了索勋,夺回了归义军政权,随即拥立张淮鼎之子张承奉为主。李氏家族没有直接夺取归义军政权,应该是吸取了索勋的教训,但归义军的大权实际上已尽入其囊中:张氏的长子李弘愿任节度副使,实际掌握归义军权力;次子李弘定出镇瓜州,任瓜州刺史、墨离军使,控制了归义军东面门户;第三子李弘谏任甘州刺史;第四子李弘益任左神武军长史,主管沙州事务;兄弟四人互为表里,基本掌握了归义军从幕府到地方的一切权力。
张氏与其子杀死索勋后,立即派使节向朝廷报告情况,但朝廷并未授予张承奉节度使一职,由此可见,朝廷对张氏家族依然心存疑忌。
张承奉虽被拥立为节度使,但其境遇与索靖统治期间相比,并未改善多少,只不过是李氏家族的傀儡而已。李弘愿兄弟将其当作泥塑木雕看待,但凡军政事务,包括使节安排、官职任免、刑狱诉讼等,均由李弘愿兄弟一手包办,张承奉唯一可做的事情,便是在各种佛事活动中为其姑母及表兄祈福。在乾宁二年(895年)除夕之夜驱傩打鬼仪式上,众人所唱的《儿郎伟》曲词中,称颂的对象也不再是节度使,而变成了张氏及李弘愿兄弟。曲词中唱道:“自从长史领节,千门乐业欣然。司马兼能辅翼,鹤唳高鸣九天。”又道:“太夫人握符重镇,郎加国号神仙……长史大唐节制,无心恋慕腥膻。司马敦煌太守,能使父子团圆,今岁加官晋爵,入夏便是貂蝉。”无一句提及张承奉,作为节度使的他反而还要屈意奉承,以示自己毫无怨言。这是李氏家族极盛时的颂歌,也是这一家族最后的挽歌。
这首《儿郎伟》无疑是李氏家族的政治宣言,在后世发现了一张落款时间为乾宁二年十月的牒文,上面已经没有了张承奉的签名,而是由李弘愿独自签署,并盖上了一方“沙州节度使印”。当时的种种迹象都表示着李弘愿等人不再甘心隐藏于幕后,而是准备走上前台,正式以节度使的身份接管瓜沙二州,行使权力。李氏家族的大权独揽早就让沙州其他大族十分不满,这样的行为无疑更是火上浇油。李弘愿等人以为自己兄弟四人大权在握,地位固若金汤,心中不免骄矜,却不想盛极则衰,变生肘腋。乾宁三年(896年)春夏之交,沙州再次发生政变。张承奉在本家族及其他沙州大族的支持下夺回了失去的权柄,而李弘愿兄弟在失去权力后先被贬官,随后被杀,只有任职瓜州的李弘定因为不在沙州,故幸免于难。
张氏由于是张承奉的嫡亲长辈,保住了性命,但她眼看着儿孙凋零,自己却苟活人世,茕茕孑立,回想当年风光,只剩下无限悲凉。四年之后的光化三年(900年)六月,她在一卷《金光明最胜王经》上这样题写道:“弟子女太夫人张氏,每叹泡幻芳兰,不久于晨昏。嗟乎,爱别痛苦,伤心而不见……谨为亡男使君、端公、衙推抄《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慈母追念,崇斯胜缘。咸此善因,皆蒙乐果。”
张氏抄完经卷的两个月后,朝廷正式任命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不过此时的大唐王朝在藩镇混战中已经名存实亡,即将走向命运的终点。这一年四月,雄踞中原的强藩朱全忠出兵河北,连战连捷,至九月,河北四镇——魏博、成德、义武、幽州皆羁服于朱全忠。此役过后,朱全忠威震河北,一举奠定了对死敌李克用的优势。朝廷方面同时又生变故,唐昭宗与宰相崔胤日夜谋划尽诛宦官,宦官皆惧,十一月,神策左军中尉刘季述率禁军入宫,囚昭宗于少阳院,矫诏立太子为帝。消息传至朱全忠在定州的行营,他立即南还汴州,此时刘季述的使者也来到汴州,“许以唐社稷输之”,朱全忠犹豫不决,召集僚佐商议如何应对,不少人都认为:“朝廷大事,非藩镇所宜预知。”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却一语道破天机:“王室有难,此霸者之资也。今公为唐桓、文,安危所属。季述一宦竖耳,乃敢囚废天子,公不能讨,何以复令诸侯!且幼主位定,则天下之权尽归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
虽然此次政变在次年(天复元年)正月即被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平定,昭宗复位,但朱全忠的野心已不可遏止,自此便开始了翦灭唐廷的计划。他先是攻下了河中镇,控制了这一咽喉要地,随后又遣六路大军攻伐河东李克用,虽然最后因疫病退兵,但河东实力大损,“自是克用不敢与全忠争者累年”,“当是时,自蒲、陕以东,至于海,南距淮,北据河,诸镇皆为朱全忠所有”。十月,朱全忠大举出兵,直指长安,宦官韩全诲见势不妙,挟持昭宗逃往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处。朱全忠以迎驾为名讨伐凤翔镇,连败李茂贞及各路援军,迫使李茂贞于天复三年(903年)正月交出了天子。次年二月,朱全忠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八月,遣亲信弑昭宗,立辉王李祚为帝,是为唐昭宣帝。907年,朱全忠篡唐称帝,建国号为梁,改元开平,史称后梁,统治天下将近300年的大唐王朝就此灭亡。
在朱全忠渐移唐鼎之际,归义军因僻处一方,未卷入中原纷争,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在朱温弑唐昭宗后,张承奉仍然使用着昭宗的天复年号,而没有使用昭宣帝的天祐年号,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对唐王朝的忠诚。904年,唐昭宗在朱全忠的逼迫下迁都洛阳,长安城就此失去了帝国首都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央王朝与河西的联系更为渺茫,归义军对朝廷的依靠成为泡影。“自从宇宙充戈戟,狼烟处处熏天黑。”回鹘趁归义军自张淮深被杀以来连年动乱,完全控制了甘州,后又得到了唐王朝的册封,正式建立起甘州回鹘政权,切断了归义军与中原的联系。西州回鹘则占据了伊州,形成了对归义军的东西夹击之势,肃州、凉州等地的归义军势力也被先后逐出。日渐强大的回鹘政权不断入侵瓜、沙地区,威胁着归义军的生存,中原王朝又无力西顾,这使得张承奉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来收拢河西民心,凝聚团结一切力量,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共抗回鹘入侵。
909年,张承奉在唐室沦亡、山河易主的背景下,先是自称拓西金山王,后来又在瓜、沙二州大族、耆老的支持拥戴下,正式建国称号,定国名为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尊号为圣文神武白帝。熟悉香港喜剧电影的人肯定会记得,周星驰1996年拍摄的古装喜剧片《大内密探零零发》中,由李若彤饰演的那位神秘美女琴操便自称来自金山国,如据此推断,那该部电影的时代背景应当是在五代后梁政权统治期间。
西汉意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即今阿尔金山,当时称金鞍山,所谓西汉金山国,实际上便是金鞍山下的西部汉人之国。同时,根据五行观念,西方属金,其色白,故张承奉称白衣天子。西汉金山国建国之初,为了制造舆论,张承奉又找人编造了白雀献瑞的神话,以表示自己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当时沙州诗人张永进曾写《白雀歌》以纪其事,该诗在民国时期被人在敦煌千佛洞文书中发现了抄本,再次流传人间。作者在诗前的序文中称张承奉“上禀虚符,特受玄黄之册,下副人望,而南面为君。继五凉之中兴,拥八州之胜地……承白雀之瑞,膺周文之德”,所以他才写下《白雀歌》。在诗的最后他这样赞颂道:“自从汤帝升霞后,白雀无因宿帝廷。今来降瑞报成康,果见河西再册王。韩白满朝谋似雨,国门长镇压敦煌。”不过,张承奉建国称帝乃是加强内部团结的自救措施,在内心中,瓜、沙二州的百姓依然向着中原,并将中原王朝作为自己的宗主。
当时瓜、沙地区北有达怛,南有吐蕃,东西两侧则是回鹘政权虎视眈眈,可以说是四面皆敌,形势险恶。西汉金山国立国后,便将统一河西、建立以汉人为主的安定之区作为国策,随之开始了对外征伐之战。在后世发现的时任西汉金山国宰相的张文彻所著《龙泉神剑歌》中我们发现,张承奉的目标不仅仅是恢复其祖父张议潮时代归义军的旧有疆土,他甚至梦想开疆拓土,建立一个东达河兰广武城、西至天山瀚海军、北临燕然山、南至青藏高原的西域强国。为了实现这样一张宏伟蓝图,张承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打通丝绸之路南道,恢复与于阗国的联系。当时西州回鹘已经控制了楼兰地区,阻断了归义军通往于阗的道路,并开始进攻与西汉金山国历来交好的璨微国(仲云人建立的小国)。于阗国是西汉金山国的盟邦,张承奉还娶了于阗公主为妻,他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必须得到于阗的支持,恢复两国交通势在必行。于是,他命紫亭镇遏使张良真为先锋,宰相罗通达为主将,率领精兵长途奔袭楼兰。金山国军在跨过“长途暗碛,鸣沙俱惑”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后,来到罗布泊畔,连续攻下位于楼兰地区的多座城池,随后又乘胜北上,来到雪岭之南、伊吾之北,欲乘胜收复西州回鹘控制下的伊州,但未能攻克城池,只能无功而返。此次出兵虽未完全实现战略目标,但楼兰之捷无疑极大地鼓舞了西汉金山国军民的士气。不久后,西汉金山国在楼兰地区恢复了石城镇,设石城镇遏使,并派兵驻守。
镇”为地方行政机构,萌芽于五胡十六国时代。后秦时,军镇正式成型,错落设置在各地的军镇有实土、有军士、有领民,正式成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北魏时期,在沿边及各军事要地广建军镇,长官称镇将,地位在刺史之上。太和年间,北魏孝文帝开始改革,他下令迁都洛阳,锐意汉化,镇的地位遂一落千丈,大量军镇被改为郡县,尚保留下来的沿边军镇中,戍边将士的待遇也骤然下降,由“国之肺腑”沦落为地位低下如奴隶的府户。将士们自然对这样天差地别的变化不满,对朝廷及掌控国政的士族的仇视最后导致了“六镇之乱”的爆发,北魏统治濒临崩溃。孝明帝不得不于正光五年(524年)下诏将沃野等六镇及御夷、高平、薄骨律等镇全部改为州,除了因犯罪被发配边疆的,其余府户全部释免为平民,只有三堡、盘阳、榆中等七个镇保留了下来。北齐、北周时期,虽然又设置了一些新的军镇,但已不管民政,只负责军事,地位也比州要低。隋唐沿袭周齐旧制,天下设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五,但上镇兵力不过五百,与北魏前期动辄万人的镇兵数量相比远远不如。《新唐书·志第四十》记载:“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可见镇是最小的。
唐中后期,天下广置藩镇,镇的数量也普遍增加,节度使往往派遣心腹将校于各都邑、关津、险要长期驻守,监视刺史、县令,这些镇将们也成为节度使的权力基石。此时的镇将,管理区域虽比县小,但地位与县令相当。张承奉时期,归义军至少有7个镇,分别是新城、紫亭、雍归、悬泉、寿昌、玉门、常乐,加上新恢复的石城,则是8个镇。后来,为了抵御日渐强大的甘州回鹘,又将玉门镇升为玉门军。
楼兰之捷后,为了实现“永霸龙沙截海鲸”的目标,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西汉金山国君臣发起了对甘州回鹘的战事。《龙泉神剑歌》详细记载了这期间发生的多次战役。
910年初秋时分,西汉金山国主动东进,发起了收复肃州的战事。金山国大军很快攻至金河东岸,在那里遇到了甘州回鹘军队的强力阻击。双方列好阵势,只见“战马铁衣铺雁翅,金河东岸阵云开”。战斗中,先是骁勇的金山国先锋将领浑鹞子率部直冲敌阵,希望搅乱对方的阵势,为己方的胜利奠定基础,回鹘军也十分悍勇,与浑鹞子等人杀作一团,抵死不退,把浑鹞子困在了阵中。为救援浑鹞子,金山国另一骁将阴仁贵单枪匹马冲入敌阵,凭借过人的武力杀开一条血路,但依旧无法取胜。最后回鹘军人多势众,金山国军饮恨败北,只得退回沙州。
甘州回鹘随后大举反击,引火烧身的金山国军迎战不利,节节败退。战火很快蔓延至沙州城下,回鹘大军在城东、城西、城北三面发起了攻击。危急时刻,连张承奉也不得不穿上铠甲,亲自披挂上阵,带领金山国全部军队一万人与敌军决战于城东的千渠三堡一带。激战中,押衙兼鸿胪卿宋惠信“当锋入阵”,连大内支度使张安左等内臣也投入了战斗。经过一番殊死血战,这才击退了回鹘人的入侵,但金山国无疑损失惨重,沙州城外的村庄、水渠、农田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次年,甘州回鹘再次大军压境,双方在城东便桥一带展开激战,金山国军此次由宰相罗通达压阵,此时已升任金吾卫将军的骁将阴仁贵再次当锋直入,押衙张西豹也冲锋陷阵,与回鹘人展开了激烈的短兵肉搏,最后击退了回鹘人。此次胜利使金山国君臣上下再次欢欣鼓舞,并喊出了“藩汉精兵一万强,打却甘州坐五凉。东取黄河第三曲,南取雄威及朔方。通同一个金山国,子孙分付坐敦煌”的口号。大臣们还建议张承奉借此次胜利,改年号,挂龙衣,举行修筑天坛、祭拜南郊的仪式。但甘州回鹘毕竟强大,单靠金山国的万余人马是很难将其击灭的。此役胜利后不久,张承奉即命罗通达前往吐蕃搬取救兵,希望借助吐蕃人的力量共同对抗回鹘,收复甘州。《龙泉神剑歌》则在对未来光明前景的希冀中就此结束。
尚未等到吐蕃人的援军前来,回鹘人的大军已于七月再次杀至沙州,此次回鹘人的统兵主将乃是可汗之子狄银。金山国军再次在城外迎击敌军,希望能够复制前面两次战役的成功经验,但胜利的天平不再向金山国倾斜。这次战役西汉金山国战败了,而且是惨败,出城作战的军队损失惨重。虽说张承奉可以继续笼城据守,凭借坚固的城墙抵挡住回鹘人的下一波攻击,但回鹘人连续三次攻至沙州城下,已经让仅有瓜、沙二州的这个小国元气大伤。“沿路州镇,逦迤破散”,死者埋骨黄沙,生者则分离异乡,原本人烟稠密的村庄一片荒凉,过去灌溉着这片土地的水利设施残破不堪,连绵战火让农业生产不得不停止下来,张承奉即使能打退回鹘人的这次进攻,那下次呢?
面对“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的惨象,张承奉只得选择低头,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他派出了宰相及高僧作为金山国僧俗两界代表与狄银进行谈判。狄银却有心折辱金山国,称只有张承奉出城跪拜,才可以谈缔结和约之事。最后,张承奉被逼得没办法,只得辩解道:“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岂有不拜父亲,先拜其子的道理?”并称只要甘州正式的使节一到,他肯定会面东跪拜。狄银听后觉得有理,张承奉这才算是过了这一难关。最后金山国以“沙州百姓一万人”的名义,向回鹘可汗献上状文,称若可汗同意谈判,将派遣宰相、高僧、贵族、耆老前往甘州,商谈具体事宜。由于文献资料缺乏,最后谈判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金山国必定是接受了屈辱性的条件。
曾经的雄心壮志一下子成了梦幻泡影,张承奉心中自然苦涩不堪。心灰意冷下,他在战败后不久将国号改为西汉敦煌国,只将自己作为敦煌一地之主,放弃了一统河西的计划。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夏,张承奉带着无尽悔恨死去,张氏家族的统治也同时被颠覆,曹议金成了沙州的新主人,归义军的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
全部回复

评论区开荒,我辈义不容辞
来抢第一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