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冀西南林路行;前卫摇滚的复古,中文摇滚的新篇
《冀西南林路行》是中国河北石家庄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以下称万青)独立发行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也是时隔其同名专辑发行近3700天后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对于这支在内地以及台湾地区都颇具传奇色彩的乐队来说,以录音室唱片的形式发布任何作品都是业内的重大消息。加上其向来惜字如金的行事风格,我们这些良莠不齐的爱评论的听众一听闻新专辑问世就赶紧先给套上“千锤百炼”、“十年磨一剑”这种听起来壮志凌云抱负远大的形容词。
快节奏新媒体短视频的年月,爱自诩时代清流的摇滚乐守旧者们翘首以盼,这几年也算拉帮结派形成了组织,聚集在各大以文艺著称的app里。有人乘飞机铁路赶去过他们的现场;有人把他们的歌在自己的吉他贝斯小号萨克斯上信手拈来;有人十年了还没把第一张专辑的九首歌听完过。他们都聚在一起,渴望万青来当自己审美的救世主。放眼中国摇滚史,期待值如此之高的专辑竟也屈指可数。
数字专辑发售已过48小时。22元单价,30余万张销量,对于中国摇滚乐队来说已经算是顶级流量,尤其还是一支几乎不接商务也从不参加节目的乐队。可以说,一方面,多年来仅靠人们口口相传积攒的人气和口碑印证了一点:至少在今天,中国音乐人靠实力仍然可以站着把钱给挣了;另一方面,高人气如原上风般掠过,卷来万千路边跟随者,那么作品本身的功过是非也终究难逃百家之口。
虽说张三李四之言并非任何程度上的指导性意见,但专辑听罢产生的满足或失落背后,却也是至少30万人的情绪波动。那么《冀西南林路行》(以下称《冀》)是否仍然是符合万青水准的专辑呢?
怀着这样一个问题,我开启了两天无休止的循环播放,寻找属于我自己的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冀》是一张到典型到不能再典型的概念专辑。按照英文维基百科的解释再结合我自己的翻译,概念专辑指的是一张专辑所有乐曲通过共同呈现反映一个中心主题,并且比起各支乐曲分开单独呈现要更加富有意义的音乐专辑。(“A concept album is an album whose tracks hold a larger purpose or meaning collectively than they do individually. This is typically achieved through a single central narrative or theme.”)概念专辑本身作为一个音乐学里相对主观的概念,即使是世界范围内的知名例子,通常展示出的主题效果也以抽象派为主。而这张专辑反其道而行之,清晰直白地告诉你主题——“冀西南林路行”,通俗理解即为“太行山游记”。在核心明确的同时,歌词里的意象也十分具体,同时重复性强。歌词里“乌云”、“雷声”、“荒原”等字眼几乎连绵不绝,山河鸟兽风林雨石的印象也一直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关于这点,词作者、贝斯手姬赓去年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就已提及:
““有听众觉得,歌词里,乌云、雷声这些意象,用得有点频繁?”
他抬起头。“就是故意的。可以把这些理解成一个舞台的布景,设定性的词汇。我就是要重复到你特别讨厌,或者读出我想说的信息来。不过现在看来是讨厌的(声音)多咯。”姬赓自嘲。”
(音乐人丨万能青年旅店 并肩莽莽原野荒2019-06-13)
相比第一张专辑,《冀》的视角和格局其实安放得更加踏实,探索的范围也更小更集中了。比起首专万青东拼西凑的音乐类型以及复杂多变的情绪表达,这一次的大体框架则搭得无比牢固。就算没有姬赓的序文说明,你也可以明显地察觉到这张专辑是一个有着长期规划的命题项目。这一次万能青年旅店不再讨论空中楼阁云中漫步,而旨在讲好一个来自华北地区的故事。
其次,器乐表现上,《冀》相当大程度受到古典交响和爵士共同的影响。先是无限放大了管弦乐的作用:萨克斯、长笛、单簧管、大中小提琴和低音提琴均扮演了关键角色。人们熟悉的小号手史立的小号作用则有些许削弱,不再频繁挑起独奏的重任。虽然小号依然算得上是诸多管弦编曲中的重要一环,但像《秦皇岛》中那样在听众印象中最能代表万能青年旅店的小号爆发声则被选择性地舍弃了。
而归根结底,万能青年旅店的血肉还是董亚千的吉他。放到专辑内讨论,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木吉他的部分增加。甚至可以说,原声木吉他的旋律感几乎起到了引领专辑情绪走向的作用。《泥河》、《采石》、《山雀》三首填词曲共通的地方在于,它们竟然均是借木琴的旋律推动前进的,电琴则是在曲目过半后才出现,用来透露情感或故事的递进。尾曲《郊眠寺》则自始至终由木琴简单的扫弦完成。
近年的董亚千愈发接近琴痴的状态,连续购入一把把新琴也是常态,未曾料到音乐制作和录音的重心反倒由电吉他转到了木琴。本以为二千老师拿手的长段电吉他solo会频繁出没,但纵观整张专辑也只在倒数第二曲、专辑的顶峰《河北墨麒麟》最后的爆发中有过一次露面。看似不合常理之举,思来想去,我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样的手段与技法不是刻意而为之。
说上面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强调一点:和处女专辑比,《冀》在主动求变,而且是巨变。如果形容一专叫风格多样,二专则可以拍板性质地被称之为一张前卫摇滚(Progressvie Rock)专辑了。相信任何听过King Crimson的乐迷,都很难不从《冀》中窥探到这支70年代英国前卫摇滚乐队的身影。一样的古典色彩,一样的声学实验;一样的庞杂典雅,一样的深邃诗性。他们自如地收敛跟释放张力,好似掌握了返璞归真的秘诀。
前卫作为摇滚学派中的一个小支流,即使在西方世界也因为艺术成本远不及市场回报而淡出主流,它如此古老,可对于我们来说却又如此陌生。未曾想,在近50年后的华北平原,前卫摇滚却得到无比虔诚的重新演绎。
十年的时间,我们等来了一场陌生文化的复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专辑开篇曲《早》是一首1分23秒的纯管乐曲。重复的这句旋律,在专辑后面会多次变形再现。按照古典音乐的专业说法,这一个乐句是为整章的leitmotiv,中文译作主导动机。德国歌剧家理查德瓦格纳提出的这个概念,指的便是一个贯穿整个音乐作品的动机乐句。
2.《泥河》是一首旋律不太上口的歌,也是歌词信息最大的一首歌。可能也因此,听众的反响并不高涨。然而作为感同身受者,我却格外钟意这一曲。
首先,要理解这首歌,就需先意识到歌词中的“雷声”实指山间开发的爆破之音,也是自然之壮景的破碎之音。而这首歌妙就妙在故事脉络和情绪推动结合得堪称一绝。
第一段,先是原声吉他的指弹给人带来的活泼感,配合歌词描述太行山自然景色之舒展。此时雷声只是“隐隐”,所体会到的是夏日来临;
第二段,鼓声起,提琴悠扬,歌词则绘出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与和谐共处。此时仍旧是隐隐的雷声,但似乎暗示着明日不详的未知;
第三段,木吉他更加明快的节奏型与高把位更复杂的和弦进行,则完美契合着歌词所述的开发商与施工队的活动。管弦乐编排开始抒情起来,雷声也变成了“阵阵”,危险已然降临。段末,电吉他以纯噪声的形式第一次出现,造成一股不适之感;
第四段,一切都变得喧闹起来,歌词却简单了许多:“乌云汇合,乌云高空踏步。再生泥河,就投身激流冲水坝”。短短两句实际上暗示的是自然治理的失败与自然之怒的后果。含沙量很大的河流,在两岸河谷开阔、平缓的河段,泥沙大量堆积,河床不断抬高,水位也相应上升。而歌词三遍的重复就像是在发出警告一般,饱含着扼腕的决绝。此时此刻,雷声变得“滚滚”,象征天罚的“怒潮”也已来临。
《泥河》表面的轻快与洒脱中暗藏着愤怒与悲壮,这也成为了全专辑里一个重要的情感谜底。而之所以说感同身受,是源于我高二转学去长沙就读的高中对面,也有一座被填平炸空的山,名曰茶子山。我去的两年恰好赶上那块区域的开疆扩土,唯一一次亲眼目睹山与楼的更迭换代,心情之震撼难以言表。
3.《平等云雾》是一首器乐,但如同曲名,这无疑是全专最朦胧的作品,甚至可以称之为一首无调乐。1分26秒的时间只是电吉他失真的杂音和背景里有些神秘的打击乐,再加上时不时出现的几个不成曲调的扫弦。我百思不得其解,遂把它看作是《泥河》的延续,作为灾难或是悲愤的冷却。这样的处理方法让我想起King Crimson的Moonchild以及The Talking Drum,希望不是我在胡吣。
4.《采石》一定是听众最熟悉的作品,因为早在5年前万青便写出了这首歌且正式在音乐节演出过了,当时这首歌的名字还叫《冀西南林路行》,正是专辑名。这也一定是乐队为新专辑写成的第一首歌,因为前面提到的专辑leitmotiv乐句其实就是来自于这首歌。然而,等到专辑版正式问世,人们才发现,原来改动和变化如此翻天覆地。
如果你搜五年前这首歌的演出视频,会发现专辑版没了那支无比性感的萨克斯。这一下子,仿佛一切都空下来了。当时被视为全曲灵魂的萨克斯演奏被抽走,却并没有任何其他同等魅力的乐器填补这块空缺,就连电吉他都给换成木的了。似乎唯一不变的只有姬赓留下的这首被我们这帮人五年来当经文供着的词作。
既然说到这首歌的词,那么不妨提一句,如果你仍然还未参透其深意,那你一定是还未把第一人称带入太行山上的一块石头的视角。我甚至相信歌名改至《采石》其实便是为了方便听众去理解和感悟。一块石头在采石场的轰鸣中变成一滩石灰,被搅拌在更大的一滩石灰里,在时代洪流中迷失方向。而这石也恰恰是人,在城市、异乡被固化跟同化,磨平了全部的棱角,甚至丢失了表达愤怒和不安的权利,最终失去了属于自我的一切特征与性格。如果去做阅读题,我理解的这首词更高的一层意思即是:人与自然之物,并非相互依存相互庇护的契约关系,因为人就是自然,自然也就是人本身。
那么再说回来,为何《采石》的编曲要如此大道至简呢?也许乐队还是希望减去这首歌的浪漫主义色彩,更多地留下太行之石朴素而普通的形象。退一万步讲,所谓万青层面的“简单”编曲,高级味仍然很重,只不过更像是一首不插电罢了。
后半部分的爵士钢琴solo,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意外。毕竟在万青的歌里听到钢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仔细想了想,应该说是没有先例的事情。至于它扮演的角色,我的浅薄之见只能提供两种解释:一是结合故事背景助纣为虐强调人为的破坏;二是这里干脆把爵士乐当作一种人造文明的虚假和谐,看似绅士高尚的音符律动中却有盖不住的采石般的剥削噪音。
再插一句,最后那几声小号,实在是让我再次想到King Crimson,这一次则是他们的名曲Starless。
5.《山雀》与《绕越》在我看来完全就是合起来的一首歌,只不过作为A部分与B部分隔开了。专辑整轨中两首歌也的确是像概念专辑的惯用招数一样无缝连接的。《山雀》的旋律优美至极,配合音色近乎柔和到犯规的长笛和单簧管,无疑将会成为整专传唱度最广的歌曲。“爱与疼痛,不觉茫茫道路长;生活历险,并肩莽莽原野荒”或许也将在下一个十年中的某一段时间成为社交媒体疯转的文字。可是如《泥河》一样,表面的温暖与柔情中,却也藏着“火光忷忷“与“盗寇”这样充满敌意的字眼。
《绕越》,不仅是一首快节奏器乐,懂音乐的听众细心点可能会发现,这竟然还是一首标准的现代进行曲——2/4拍、120BPM。
也许,专辑的一大暗语便藏在这里。
进行曲又名行军歌曲。说到这里,你还记得《山雀》的最后一句歌词吗?
“火光忷忷,指引盗寇入太行。”
话音刚落,盗寇们便成群结队行军赶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绕越》正是在对这场资本对资源的抢掠豪夺进行生动的诠释。这含蓄的讽刺方式被破译发现的瞬间,竟然还有些让人忍俊不禁。
6.终于到了《河北墨麒麟》。这是一首由作词作曲演唱到编曲录音混音都处在俯瞰视角的伟大作品。管弦乐、电吉他、贝斯、鼓,没有一处拖了后腿,没有一个地方多余。随便举几个例子:董亚千几乎不带感情的声线似乎能让你听到那神兽墨麒麟俯视人间的不屑;节奏上,五拍子和四拍子上的自由转换洒脱到令人来不及发现;那段管弦乐长riff的线性质感美学,则是缺乏基本功与艺术素养之流怎样模仿都创作不出的。这也是迄今万青问世的作品里艺术造诣最高的那一支,没有之一。我相信他们自己也不会否认。
其余无须赘言,十年后再回顾此曲,你会发现它一定站在比《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更高的维度,虽然今天的你或许并不认同。
7.《郊眠寺》其实可说的并不多,这其实是我相对而言最不喜欢的一首作品,因为相同旋律相同和弦出现的时间过长,但这也纯粹出自我个人的偏爱喜好。这首歌更像是一首bonus track,在主故事讲完后,留下的一个后记。董亚千与姬赓就像一部纪录片的冷酷旁白,在节目尾声突然划开了第四面墙,藏起情绪起伏波动,娓娓道来一些细碎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leitmotiv主导动机乐句再次变形出现,首尾呼应为专辑画上句号,使《冀》的全轨形成一条闭合的回路,由圆形轨道的起点开上一圈到达终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也许人们不会想到,一张专辑的事情,一个乐队居然真的花了十年的时间,就像也许人们不会想到,一个不属于摇滚的时代,居然也有一个乐队能一天卖到600万销售额。即使人群的本意并非均是为今日的《冀西南林路行》付款,又或许更多人只是寻觅一个为过去买单的契机。可即便是出于音乐爱好者的角度,看到人们愿意为高价值的作品去当一回消费者,也是足以欢颜之幸事。无所谓现在的你我是否有足够的欣赏高度,但至少欣赏的渠道和平台就在这里。
这说不定也将成为万青无意间的功劳。未来的十年,也许会有无数的中国乐队——尤其是青年乐队,去以万青的标准来对待摇滚乐,创作摇滚乐。那么,就算万青下一张专辑又要等十年,中文摇滚也从此时此刻起,迎来了它新的篇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了,之前我抛出了问题:《冀西南林路行》是否仍然是符合万青水准的专辑?
我已有了我的答案。
这些回复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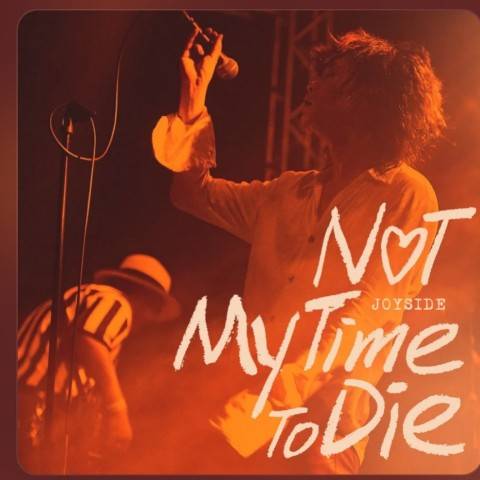
红旗街的夏天
· 河南虎扑因为有这样的帖子水准才能上升,但是也如我所料,垃圾撕逼贴吵几百页,这样的好帖子没几个人看

翻译什么是惊喜
· 山东引路人很重要,不成功就没有人喝彩,也没人追寻。万青的这种创作态度无疑会影响后来人,路会越走越宽。无论是师法70年代的前卫艺术摇滚,还是观摩当代电子网络世界的光怪陆离,创作从来都不是为了迎合听众,而是为了引导真相,探索艺术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