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简单影评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首映于1991年,是张艺谋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而成。同张艺谋九十年代的早期电影一样,贯穿着张艺谋独特色彩效果和特有的历史文化沉重感,同样穿插了大量的奇观民俗元素。影片主要讲述巩俐饰演的颂莲被送进陈府成为四太太,大红灯笼与捶脚成为太太们被临幸的标志,颂莲起初得到老爷宠幸,但却被二姨太挤兑,颂莲因涉世不深,生性叛逆的她设计被看穿,最终酿成悲剧的故事。
影片充满了极多的象征手法,最为明显的便是“灯笼”与“捶脚声”。而此时的张艺谋叙事还极为简洁干净,大多交代都利用象征手法带过。在色彩运用上,张艺谋还是坚持了自己特点,几乎不使用过渡色,大面积的色块儿给予了极强的力量和压迫力。整部影片拍摄场所较为单一,但单一的场所并不影响其思想表达,反而更加契合了其主旨。
镜头与构图
影片的镜头简洁不花哨,更是使用了不少的固定机位中远景来处理。构图上,大量利用屋檐、门窗进行了封闭式框架构图。而主观镜头,中远近景的切换流畅自如,都给予了一种压迫、窒息的感觉。
影片一开场就连续用了三个骑轴摄影、两个固定机位镜头。在张艺谋的作品里,这样连续使用固定机位是很罕见的事情,但一查监制是侯孝贤时,便就释然了。连续的固定机位镜头将人物卡死在镜头中央,给予了观众强烈的压力。
骑轴摄影带来了穿越墙壁的效果 让巩俐的情绪放大到更大 直击观众
而第一次陈府的环境展示便更是将中式传统院落展示的淋漓尽致,轴对称的构图设计和屋檐相连而形成的封闭式构图将外部环境不言而喻地表达出来。
代表封建旧势力的管家和颂莲之间的人物位置关系 已经在第一次碰撞时 便交代了颂莲最终的命运结局
而在室内戏时同样利用中式家具下的门框窗户成为天然的框架道具,一次又一次构建起封闭式框架构图。
陈府全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起吃饭
在这个镜头中,不仅构造出了框架封闭式构图。还使用了一个远景,留出了纵深,并尽可能保证了对称。轴对称对应了封建礼教下的“规矩”,张艺谋利用影像无时无刻地给予观众这种“规矩”带给人的压抑感。
或许因监制是侯孝贤,张艺谋在此片中的一些片段上放弃了激烈戏剧冲突的表演和强烈的演员情感输出,用了一些中远景镜头过滤了戏剧性。
老爷烧掉了父亲留给颂莲的遗物——笛子
这一场戏码可以处理得带有强烈的情感爆发,但张艺谋连一个特写,甚至近景都不给。远景之下,双人对峙、不说话,反而更有窒息感。归于剧作,将片头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颂莲安静化处理,体现了封建势力逐渐扭曲了其抗争本性。这样的处理,颇有侯孝贤的“隐”字美学。
色彩与光影
影片在色彩上完美诠释了张艺谋的视觉美学,全片几乎很少使用过渡色,在大量的红、黑、白、蓝四种颜色上交替使用。
红色,传统上认为是喜庆吉利的颜色,但也正因传统所致,带给了片中几位女性无尽的束缚。
蓝色,象征着传统的封建势力(这里同张艺谋在之前的作品《菊豆》中所用一致)。
白色,则是凄凉、冷漠。
黑色,则直指死亡。
四种颜色下的陈府显得阴森而恐怖 压抑又绝望 配合着封闭式框架构图 给予了无法逃脱的窒息感
雁儿被冻死在院内 雪的白是她的凄凉 缩成一团的黑 是她的死亡 被蓝色笼罩的环境 是指出杀人凶手——封建势力
全片在用光上较为均匀自然,没有太多特别的使用。但在颂莲与飞蒲相见时的打光,成为了全片最为人性的片段。
这一个片段成为全片中最为人性 最为温馨的片段
颂莲因笛声而被吸引到天台,随之与飞蒲相见。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此刻相遇,给了颂莲一个侧光,并进行了柔光处理,还用浅焦镜头虚化掉了身后背景。这一场戏其实传递出了诸多信息。
一道侧光和柔光处理,就像是给了颂莲压抑黑暗的生活里一道希望的光,她在此刻遇上了一个同样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但两人的身份和位置差异,本质上还是封建势力的束缚导致了二人的不可能。所以最终,张艺谋用了一个相似镜头的对切结束掉了这一场戏。
注意 两人依旧被门框所框住 黑色的门框代表着封建势力的制约与束缚 而二人完全相反的侧身方向则代表着两人完全相反的人生轨迹
长长的黑色廊坊 五个黑色的窗洞 成为了二人的隔绝 影像所传递的信息胜于一百句台词
而紧接着就是老爷烧掉了颂莲的笛而彻底让颂莲死心,完成了性格扭曲上的转变。颂莲被烧掉的笛与飞蒲手中的笛形成了一组对比和连接。
音效与音乐
影片的音效使用也是一大亮点,甚至构建了音画蒙太奇。先谈音乐,影片的音乐采用的是交响组曲,基本采样的是京剧,并用女声合唱和京剧中的打击乐器构造出了音乐组合。影片的开场便使用了的是戏曲,直接给予了观众时代感和独特的民族感。因大量使用“捶脚”的邦邦声,也成为了影片的“配乐”之一。“捶脚”不仅是张艺谋早期电影中的民俗之一,在这里还有着很明显的其余作用。第一,利用“捶脚”在陈府的特殊性,用其邦邦声渲染了陈府几位太太表面是明争暗斗,实则是封建束缚下欲望体现的氛围感。第二,不断地利用“捶脚”的邦邦声给了观众节奏感,能更加顺利地带入到剧作氛围和张艺谋导演本人想要达到的观影体验之中。
而影片结束在陈府迎娶五姨太之时,此刻的音效采用了大提琴伴奏和锣鼓以及女声哼唱,不仅与片头成为呼应,也提前预示了五姨太的凄凉命运。
而利用音效构造出的音画蒙太奇,讲一处,是丫鬟雁儿身上的一处。
颂莲第一次进陈府时,雁儿在院中洗衣裳。那是丫鬟雁儿第一次出场,也是颂莲与丫鬟雁儿第一次照面。颂莲在院中蹲下用雁儿的洗衣裳的水洗手,管家在房内喊:“四太太请进来吧”,但镜头没有摇给真正的四姨太颂莲,反而是摇给了洗衣裳的丫鬟雁儿。
最巧不过的是雁儿的目光是一种寻望的目光 暗示了观众:雁儿有一个太太梦
张艺谋用一个镜头就在人物出场之时将这个人物给定了性,生为丫鬟命却有了太太梦,后面的凄惨下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大师张艺谋用其精炼的镜头语言省略了万千引导与铺垫,人物的一开场就已被大师张艺谋定好了结局。
一些象征
本片采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来处理拍摄与叙事。最为明显的就是“大红灯笼”与“捶脚”的邦邦声,这里就不再谈了。
影片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讲述,但一开始是夏,结束是冬,没有象征着生命的春。张艺谋导演或许想利用这个告诉我们,生活在陈府大院下的这群女人,没有生活的希望,她们唯一的光便是那盏“大红灯笼”。
影片中的重要人物中,只有老爷是男性,但这位唯一的重要男性人物却没有一个正脸近景镜头。这是相当巧妙的一个设计,可供解读的思路有很多。我认为,张艺谋想表达并非是老爷掌握这些女人们的生死大权,而是封建束缚。一个特写甚至近景镜头都不给的人物,并不是那么重要,他只是一个代表,真正的源头仍是封建束缚。
影片中的天台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在其他电影里,天台也是重要道具或说象征,通常下都代表着“见光了”、“自由了”的含义,如《无间道》系列、《肖申克的救赎》等。在这里,也基本上有着这层意思,比如全片总最温馨的片段——颂莲与飞蒲相遇在天台、三姨太梅珊“忘不掉从前”唱戏在天台、颂莲与梅珊敞开心扉也在天台。但大师张艺谋不会就这么简单地利用天台,他将本是具有极多“正面情绪”的天台做了一番设计,反而成为了束缚、压抑主旨的对比道具。
张艺谋将“死人屋”放在了天台,张艺谋在天台外安排的是白茫茫的天——即使上了天台也被凄惨的命运所笼罩,根本无法逃脱出去。
颂莲第一次凝视“死人屋” 人虽处天台 但头顶是白茫茫已经注定的命运 脚下是青黑色包裹的陈府大院 一席白色旗袍的颂莲 更添悲凉之意
另外,影片还有很多象征上的小细节。比如,嫁人时不坐花轿单拧一个小皮箱象征着受过教育的颂莲的清高与西式思维的影响、初入陈府时不屑“捶脚”这种权利的符号但又因虚荣不得不参与其争斗、颂莲的人生转折点为19岁父亲过世而沦为小老婆象征封建时代下女性成为男性附属——人生的变故皆因男性、初夜后颂莲照镜子——张艺谋利用“镜子道具”给出颂莲人性扭曲的开端。
整体而言,影片充斥着早期张艺谋的一贯特点,其大胆鲜明而无过渡色的用色、其承载着的时代感与民族感、其在早期电影中爱穿插使用的民俗特点都一一在列。影片也极具象征感与形式感,其大量的对称构图不仅给了影片厚重感和压抑感,也对应着传统封建下的“规矩”。在艺术、思想甚至完成度上,我都认为这是大师张艺谋生涯最佳作品。或许《红高粱》因其开创性和时代性会在中国影史上留下更为浓重的一笔,但从电影本身而言,我认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张艺谋的最好作品。
在新禧年之后,大师张艺谋拍出的《长城》、《三枪拍案惊奇》、《满城尽带黄金甲》等被骂为烂片,但我认为作为电影导演而言,不用每一部电影都拍出八十分甚至六十分,只要拍出一两部能够留名影史的作品就已足够。
PS:张艺谋是我心中除开王家卫 侯孝贤之外的华语最佳导演
简单影评系列 之前也写过几篇了 有《一一》、《少年的你》、《恋恋风尘》和《德州巴黎》
这些回复亮了

空砍帝
· 四川我同意,我觉得大红灯笼是张艺谋构图、色彩与剧本结合的最好的一部电影,看着没有任何突兀,整体性非常好,艺术水平也高。整体节奏有一点侯孝贤的味道,但是张艺谋自己的风格更强烈。这也是我认为张艺谋最好的作品,其次是秋菊打官司,然后才是红高粱了。一群人无脑吹嘘的《活着》,在我眼中和这三部电影根本不是一档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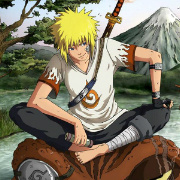
-惜琦-
· 北京这部片子看完之后就是两个字:工整,工整到极致那种,个人感觉老谋子的电影给我杜甫那种感觉,不像王家卫姜文这种极富浪漫主义,像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