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中国诗的两座高峰——李白与杜甫,我为什么偏爱后者?你更喜欢谁?
曾经看过一节岭南大学的公开课,内容好像是郭沫若,而主讲是颇有名望的许子东。课上谈及郭沫若的名作《李白与杜甫》,许子东说了这样一番话(大意是):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人都要在李杜的问题上表态,要么是抑李扬杜,要么是抑杜扬李,如果一个人是中间派,那就说明这个人还没有进入中国诗的境界。
许子东
也不怕贻笑大方,以我的一孔之见来看倒是颇认同这种说法,因为一个人如果在种问题上没有自己的“偏见”,用诸葛亮斥程德枢的话来说恐怕便是“惟务雕虫的小人之儒,笔下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没有主见、随波逐流不仅谈不上成熟,也是读书的大忌。
而郭沫若便是抑杜扬李的代表,在他的著作中,即使是那首如今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被贴上地主杜甫对穷人孩子(南村群童)吝啬的时代标签。
关于李白,他的个性与字中的纵横驰骋在诗这种体裁的承载下实在是太值得大书特书了,无论是金龟换酒还是贵妃研磨,无论是从竹溪六逸还是到饮中八仙,这位天子为之调羹的诗仙与酒仙仗剑去国、弹剑作歌、镜湖飞渡、金樽对月的姿态实在令人神往,即使是偶作闺怨,一首“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也成百代词曲之祖。连他的死也那么浪漫,水中捞月、极尽灿烂,甚至在《警世通言》中更有“一自骑鲸天上去,江流采石有余哀”的传说。
《猫妖传》中的李白剧照
无怪乎即使到如今,李白也依旧吸粉无数,连流行音乐中也唱到“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而却从未听过有人愿当杜甫。
杜甫的一生虽有色彩却无传奇,即使我仰望他的高度,却也从无念想去攀他登过的山,我们这些“温室中的金枝玉叶”哪还会有“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的担忧呢?或许正如余光中《寻李白》中所吟咏的——把满地的伤兵和难民,把胡马和羌马交践的节奏,留给杜二细细的苦吟。谁知杜甫这一苦吟却吟出了一段波澜壮阔、慷慨悲歌。
余光中《寻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依我个人的看法,初学诗的人没有不喜欢李白而钟爱杜甫的,李白诗中的天马行空很少有人能不为其折服,除此之外还有像《静夜思》与《赠汪伦》这样朗朗上口的诗篇更是家喻户晓,从幼时便熟记。在那个涉世未深、胸无点墨的年龄,恐怕少有人能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与“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样的句子中读出味道来的。
记得梁实秋的文章中记载梁启超在演讲时说到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时,涕泗横流之中张口大笑,这是熟读杜甫又事经沧海桑田之后才有的姿态与彻悟。诗人冯至的一首绝句中写道:“携妻抱子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也是至情之作。所以有种说法叫“少时读李白,壮年读杜甫”,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
诗人冯至,著有《杜甫传》一书
但是说来惭愧,我至今不过一生活在象牙塔中的穷学生,除了略知杜甫生平与熟读几首杜诗外谈不上登堂入室。可能是性格所使,也可能是口味不同,也许是自作聪明,又或许是机缘巧合,“光焰万丈长”的李杜文章,我偏爱杜甫。
李白文章中的那种纯美是浪漫的大成,但我更喜欢杜诗的沉重与力道,像《秋兴八首》与《阁夜》这样名作中的句字不必再提,在他流离的那些日子,那些他用来或排遣或倾诉的诗句更是动人,像“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像“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像“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任何一个读杜甫的人,首先要读杜甫的生平而不只是他的诗,李白的很多诗可以单独拿出来欣赏,而杜甫的诗却必须感悟其惨淡的一生。
但是杜诗又不只是这些或沉重或屈苦的悲歌或呻吟,像“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这样的诗句不输孟浩然与王维。他也有“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这样的豪情,以至于金圣叹将杜诗列为第四才子书时,在其序中引用其友人徐子能的诗,评价杜甫是——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晚年律更细,独立自苍茫。
杜甫从其早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开始,到晚年“老去诗篇浑漫兴,春来花鸟莫生愁”,他的律诗更是臻至大成,如律诗的高峰《登高》(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首),以至于明代文坛盟主王世贞称其为“圣”。到后来元稹为杜甫写墓志铭时更是称杜甫是: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意为杜诗为诗之集大成者,杜诗的魅力绝不是那“诗史”标签的以偏概全。
位于河南巩义的杜甫像
从“晓日荔枝红”到动地而来的渔阳鼙鼓,在草木春深的长安残城,用郑振铎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杜甫的评价来说:“他离开了李白、孟浩然他们的同伴,而独肩其苦难时代的写实的大责任来。”即使在湘江的客舟中,行将就木的杜甫也写下“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诗篇。
喜欢杜诗的人,大概和我一样喜欢品味他那些生活诗中的辛酸,在很多篇章之外也跟着感受他在天宝末年从终南山下的长安弥漫到天下的愁思,时而对其华章拍案叫绝,最后掩卷沉思深感用以载道的“千古文章事”并非迂腐妄言。
杜甫的死没有李白的壮美,在《唐才子传》中关于杜甫死的传说也是饿极之后吃牛肉撑死的,而杜甫应该死在南下郴州的一条船上,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他也是漂泊的,而且那时的他也还是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每次谈到杜甫我总是提到那首《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蘅塘退士孙洙评价这首诗时说:
“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具在其中,少陵七绝,此为压卷。”
或许能读懂这首诗的时候,才能开始理解杜甫。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我既听腻又反感的一句话,但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对于读者个人来说,对于萝卜或白菜也是总要有个偏好的。于我而言,红烛罗帐太过腻口,断雁西风、僧庐听雨却别有个中滋味。
这些回复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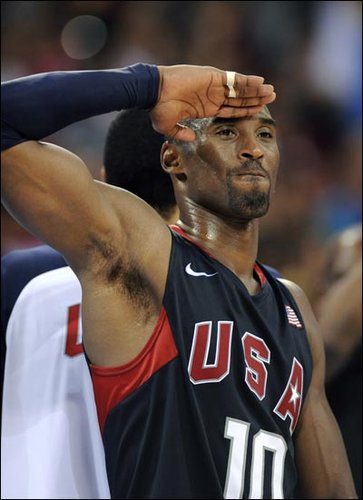
春日沙江
标题改为唐诗两座高峰更合适,中国诗歌是四个高峰,屈陶李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