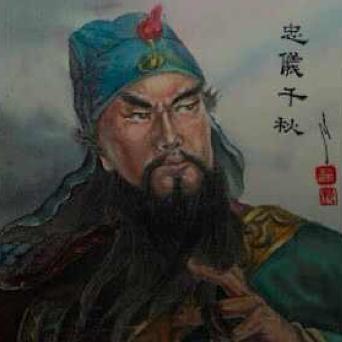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被遗忘的“九丘”:《山海经》的前世今生
《山海经》向来神秘,目前发现的最早记录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如果《山海经》真如我们推断,是西周时期的作品,那为什么先秦典籍中没有《山海经》的记录呢?
轶失的典籍
中国史料虽然丰富,但在漫长的历史,曾因为种种原因,有过大量古籍轶失的情况。其中有记载的几次就发生在先秦时期。
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因宠爱王子姬朝,想立他为太子。同年四月十八日,周景王还未立姬朝为太子,便在荣锜氏那里去世。国人拥立周景王嫡长子姬猛为王,姬朝便在贵族尹国等支持下,联合失去职位的百官和百工,举兵攻占据都城洛邑。但姬朝立五年而败,为证明自己正统地位,姬朝携周室典籍奔楚。这批包含了中华文明上古文献的珍贵资料从此消失于历史之中。
其后,由于礼崩乐坏,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把他当时所能见到的夏书、商书、周书等,涉及从唐尧一直到秦缪公一千六百年间的大事资料进行了系统编纂和整理,将许多他觉得不必流传于世的文档进行了删减,得《尚书》百篇。
到了秦始皇时期(前259年—前210年),丞相李斯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被秦始皇采纳建议,下令焚毁《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收藏《诗经》、《尚书》等也需要交出毁掉。但雪上加霜的是,在项羽攻破咸阳后,火烧咸阳宫,大火持续三个月不灭,博士馆收藏的图书终被彻底毁灭。
典籍轶失,是先秦典籍中没有《山海经》记录的第一个原因。
这些轶失的典籍当中,也许就包含有《山海经》的线索。我们现在无法确知其中内容,但从孔子后人汉代孔安国的《尚书序》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蛛丝马迹。
《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以《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书,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 皆聚此书也。"
其中的"九丘",性质和《山海经》非常相似,都是地理风物志。而自孔子删书后,"九丘"就被更专业的"职方"取代,还是《尚书序》: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
"九丘"的最后更新是在孔子之前,和我们推断的《山海经》成于西周时期的时代相符。
这些事件和记载都暗示着《山海经》和"九丘"的联系。
权力的象征
现存关于"九丘"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左传》中,是楚灵王与子革的对话:
《左传·昭公十二年》:"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有意思的是,在各种典籍中,"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通常一起出现,既是代表了上古文献,结合《尚书序》的描述,也说明了四者是官方所藏。从楚灵王与子革的对话可以看出,周王子姬朝应成功奔楚,所以,一直被称为也自称蛮夷的楚国才会有中原的官方典籍。
将官方藏书作为投诚品献出的习俗很早就有。
《吕氏春秋·先识》:"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
注意,奔出携带的是"图"、"法",其中"图"指的应就有地图,和"九丘"相关,也说明了“九丘”是迭代更新的。
我们熟知的荆轲刺秦王,记录的也是"图穷而匕首见",献城先献的是地图。
湖南长沙西汉马王堆墓葬出土的三幅中国最早的古地图《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更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入葬:
从复原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地图技术已经相当先进。
《吕氏春秋》的记载表明官方测绘作图的行为自夏就有,而做为夏朝开创者启的父亲,大禹不仅留下了治水的故事,也留下了地理著作《禹贡》。如果没有地图,大禹是无法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的。《史记》中描述了大禹测绘地形时的情形:
《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
勘测地形的技术非一日可成。事实上,如果没有地图,黄帝与蚩尤大战时即使做了指南车依然会迷路,号称"云师"更无从谈起:
《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
并且,那么大的疆域,如果不测绘记录下来,怎么知道分家后的亲戚在哪里?谁是敌人、谁是盟军?口粮在哪、兵器的原料在哪?关于民生的盐、陶,关于祭祀的玉在哪?钱在哪?如果这些都不知道,那花大力气、用那么多的牺牲打下来的领地有何意义?
《山海经》中明确记录了测绘地图的目的和必要性:
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穀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正是由于地图如此重要,在古代又获取困难,才成为了投诚品,成为了权力的象征。也因此,注定了作为"九丘"组成部分的地图是稀缺的保密资料,流传不广。这是先秦典籍中没有《山海经》记录的第二个原因。
绝版
因为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焚城的影响,多数官方藏书已经绝版,如现在流传的今、古各版本《尚书》便是由秦博士伏生在九十岁高龄时凭借记忆写出并与西汉时在孔子老宅墙壁中发现的藏书构成。所以,"九丘"的存本应只剩下陪葬用书和王子朝奔楚所携带的版本。
到了汉代,官方开始重新搜集整理古籍,《山海经》之名最早便是在此时出现,由刘向、刘歆父子校勘完成。
刘向、刘歆父子校勘了什么书,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到:
《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列传》中同时出现了“古图书”和《山海经》,并且关于“昆仑山”的记载两者一致,说明了无名的“古图书”应就是刘向、刘歆父子校勘的书籍,并重新命名为《山海经》。而从性质分析,这些"古图书"就属于"九丘"的范畴,也间接说明了《山海经》曾经是有《山海图》的。经是对图的说明,图是经的可视化,两者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但图可能由于版面过大,保存困难,已经失传。
将"古图书"重新命名,是先秦典籍中没有《山海经》记录的第三个原因,也是直接原因。
另外,《大宛列传》中还出现有《禹本纪》,《山海经》的山经部分也有“五臧山经”的别称,结合《吕氏春秋》的记载,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四者的并列关系来看,我们可以推断“九丘”应为地理志的总称,而其下,不仅有《山海经》,还有历代积累下来的旧文献。
其时,古人是将校勘后的《山海经》作为历史地理文献看待的,不仅《水经注》中对《山海经》多有引用,官方还将其作为赏赐品赐给有功之臣:
《后汉书·循吏列传》:"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
被遗忘的"九丘"
以上几点,既是先秦典籍中没有《山海经》记录的原因,也是《山海经》脱胎于"九丘"的判断依据。
不过,由于版本过于古老,记录的生物视角原始荒诞,使得《山海经》最终沦为"志怪古籍"。并且,由于"九丘"在孔子时已停止更新并被替代,使得人们认为重新校勘的《山海经》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宋·胡应麟:"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
而通过分析,我们知道,胡应麟恰好说反了。作为官方地理图书文献“九丘”中的一种,不是《山海经》录自《穆王传》、《庄子》、《列子》、《离骚》、《周书》、《晋乘》,而是周穆王根据《山海经》会见了西王母,其他各书则引自《山海经》。
全部回复

评论区开荒,我辈义不容辞
来抢第一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