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孤独的蜕变 永远值得我们等待——《孤独摇滚》三集过后的随笔
本文已入选第8期《每日必看》
什么自信之人,那样的人根本不存在,有的不过是能够假装自信的人。 ——村上春树《且听风吟》
自信和自卑究竟相距多远?也许只是隔着一条细线罢了。当你不怕失去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自信;当你害怕失去时,必然不存在绝对的自信。
今年十月,《孤独摇滚》脱颖而出,博得了不少青睐,不仅有芳文社的老观众兜底,许多新观众也慕名而来。当然故事的内核依然是美少女做着她们享受的事,而恰到好处的节奏、搞笑的环节、舒服的画风构成了她良好的观感。不过最值得一说的还是女主,波奇酱后藤一里。
在我有限的阅历重,这似乎是第一部以名副其实的社恐为主角的作品。“社恐”在当今社会是一个贬义词,而一里就像一本“社恐说明书”,把社恐的缺点铺开了展现给观众:胆小怕事,屡屡逃避,做白日梦,极度自卑,不懂拒绝。
相反,之前我也写到过,是《摇曳露营》让我重新审视了“社恐”、“内向”和“孤独”。在以上一系列缺点的背后,我也能看到一里的闪光点:她不懂拒绝,说明她善良;她自卑,总是觉得自己辜负了别人,说明她为朋友着想;她一次次地出丑,但依然不甘于现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她内心世界丰富。
这一点是《露营》的志摩凛教给我的,而《摇滚》则是把主角的全部心境都掰开了揉碎了,每周都用20分钟传达着一个讯息:我不表达不表现,不代表我不思考。
这或许引起了许多“社恐”观众的共鸣,他们时常遇到“社恐”瞬间,内心无数的吐槽,都在这部作品里以一种更具张力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也是我最乐意看到的的一点,这种形式同样在对抗着社会对“社恐”的主流看法,它在传递一种观点,或者说一种事实,即“社恐”并没有举手投降,并没有心理扭曲,他们同样在思考在贡献,同样在与矛盾的对立面做着斗争,同样在活着。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社恐”,或者说认识我的人往往评价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社牛。可我依然从这部番里得到了共鸣和反思。
开头论述了自信和自卑之间只有一念之差,而所谓的社恐和社牛,不也是如此吗?作为一个搞语言的,我早就发现自己在使用不同语言时,性格截然不同。和中国人说中文,我自然如鱼得水,嘴动的比脑子转的还快,直言不讳,毫无畏惧;和英语母语者讲英文时我便会转为被动,即便我的英文水平足够优秀,但仍比不过母语者,再加上英语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逻辑性更强,此时我只能退居二线,组织好语言后再陈述观点,而不是想什么就说什么。交过的几个美国朋友,一开始都以为我算半个“社恐”。
原因何在?见到比你更强的人,你自然会自卑,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强大;做一件事必须要有所付出,甚至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换做谁都想要逃避和退缩。区别就在于阈值,体现在社交方面,就是外向的人阈值较大,内向的人阈值较小,“社牛”和“社恐”便这样诞生了。
扯远了,回到本作,看看另外三个角色。虹夏和凉,令我想起了抚子和凛,一个是无死角的社牛,一个是我行我素的独行侠,目前没什么个人剧情,我也没看过原作。喜多,虽然只出场了一集,却已有了立体的形象。我倒是从喜多身上获得了许多共鸣,从一里的视角来看,喜多是个完美的现充,她自己都说“我最喜欢和人打交道了”。在旁人看来,她是无懈可击的社牛,但面对爱慕的凉前辈,她害羞,撒谎,逃避。光鲜的外表下,她有她的软肋。
当喜多批评自己“只会逃避,不负责任”时,一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也让我想到了我自己。我们或许比常人要自信要外向,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没受过伤。那些让我想要蜷作一团、嚎啕大哭的时刻,我无法将其抛在脑后,我能做的不过是把它们囚于内心一隅、不肯释放而已。又或者在那些脆弱的瞬间我才是我,那个自信的自己不过是我的影子罢了。
总而言之,社牛在超过阈值情况下同样会变得自卑,变得不堪一击,所以社牛凭什么能觉得自己比社恐要高一格?或许大部分观众都不会想到这里,甚至或许作者也无此意,但是这样一部刻画一名“社恐”成长的作品对我来说,就是如此意义非凡。我忍住了去看原作的冲动,并且希望接下来这部作品能让我们看到一里的成长。
如果你看到这里,就会明白,我所谓的“成长”,并不是指一里由一个内向社恐成长为一个外向社牛。如果真是这样,这部作品就毁了。她的问题不在于内向,而是在于“软弱”。性格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是否愿意去解决问题,是否能做到负责,不甘于现状时是否愿意踏出舒适圈,这些问题有着相对公认的标准,也是一里目前欠缺的。
因为作品总是将一里出丑作为搞笑环节,有些人可能会嘲笑她,如果她没有遇到虹夏这个好人对她仁至义尽,如果不是她运气好撞上了契机,一里根本不可能做出改变。
但我看到的是,在这三集里,她一集一个脚印,突破着自我,上场表演,看着客人的眼睛送饮料,主动挽留喜多。步入正轨后,等待着量变的便是质变。
“孤独”说完,再说说“摇滚”。吉他,是她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但就是这唯一的爱好,也是一里被动接受的,她也承认自己对吉他“动机不纯”。不可否认的是她的水平已经出神入化,然而她“只弹当下流行的曲子”,当问到音乐取向时,她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此看来,对现在的一里来讲,吉他更像是排忧解闷的一项工具,是一种有始无终的徒劳。
这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并没有与生俱来的爱好,大部分都始于“动机不纯”。再拿我自己举例,我喜欢打球,始于想受欢迎,我喜欢做饭,始于节省开支,我喜欢看书,始于打磨文字。爱好的关键是反馈,通过热爱收获快乐的感觉是无可比拟的。
在热爱之上,便是那种能叫人穷尽一生的悸动。毫无疑问,《露营》的志摩凛便是典范,我怀疑本作的凉也是如此。这种悸动,可遇而不可求,反正我还没遇到过,在我不断安慰自己还年轻的时候,慕然回首,人生已经过去三分之一,想要抓紧,却又无从下手,好不苦恼。所以对于本作,我还有一个愿望:一里对吉他的爱好能成为热爱,再成为终极的悸动。自己做不到的,不由得寄希望于虚拟作品。
悸动从何而来?人。虹夏拉了一里一把,她们张开双臂迎接她,传递着热爱的温度。喜多在第三集说:乐队就像家一样,一句话温暖了一里。确实,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总能擦出悸动的火花。当她们的心意合为一体时,那种悸动便会应运而生。
有的东西不过很久,是不可能理解的。有的东西等到理解了,又为时已晚。大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尚未清楚认识自己的心的情况下选择行动,因而感到迷惘和困惑。 ——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孤独的人都只是在追逐着自己的影子,不过一路上不要忘了偶尔抬头仰望,没准星光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这样的奇遇永远值得我们等待。
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更多《每日必看》内容
每日必看第8期这些回复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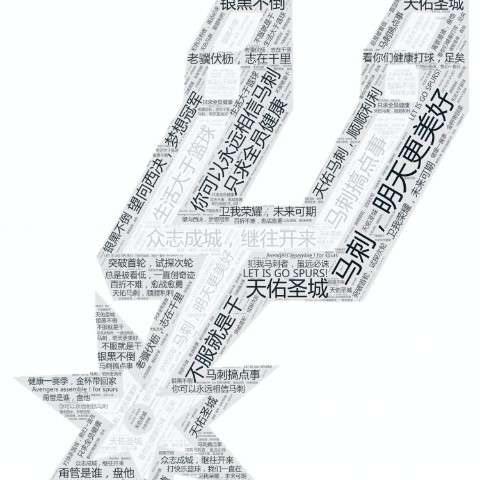
小笠原晴香基地
· 黑龙江于我而言,乐队是此生无法触碰到的光芒,却又一直闪亮着吸引我,小波吉是幸运的,幸运的她有天赋,又足够努力,幸运的她能遇到虹夏这样现实里不存在的band member🐶,幸运的她能凭借漫画与动画放大了阴角的心理活动并将其夸张化,搞笑化,我甚至想把本番称作lucky rock,或者,bond band?希望每个生活里的阴角都能拥有小波吉的际遇

伞木希美我老婆
· 广东反正让我这个卢瑟产生共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