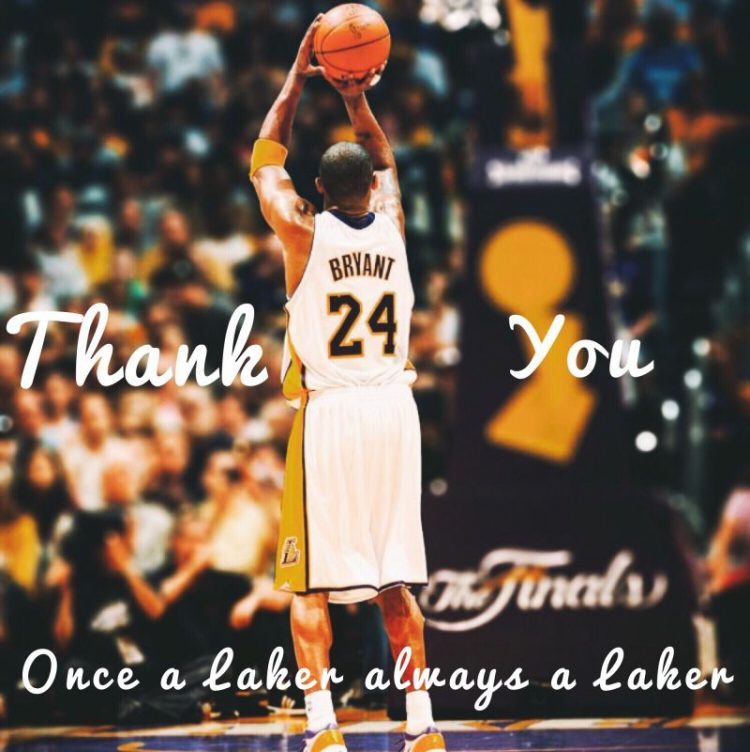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大学生屠夫”马加爵:从优等生到A级通缉犯,他的心路历程透视
“‘加爵’这个名字是我爷爷取的,他那一代还很封建,希望我当官发财。”
行刑前的一段采访中,马加爵曾这样解释自己名字的由来。他讲完名字由来后,眼里闪过一丝失落道:
“但官和钱不是我的理想,小时候想过当科学家,长大后就没有什么理想了。”
说这段话时,曾贵为新世纪首批大学生的马加爵,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毕业那年,即2004年,他在宿舍残忍杀害了四人。
马加爵(中)
马加爵曾是一等一的优等生,他并不是一个不会思考的人,在最后的谈话中,他被“理想”二字触动,所以,聊了半天后,他突然地折回到“理想”的话题,他说:
“我觉得没有理想是最大的失败,这几年没什么追求,就是很失败。”
马加爵曾经有理想,他的理想在少年时期就成型了,可后来,他的理想去哪儿了?从“有理想”到“丢掉理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得回到最初说起——
马加爵生于1981年5月,祖籍广西宾阳县,他的父亲马建夫和母亲李凤英是宾阳马二村的本分农民。
马加爵出生前,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因是超生的孩子,他一落地,家里就被罚了500元。这笔超生借款,一直到马加爵上高中时,才被还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让父母颇欣慰的是:马加爵从小就乖巧懂事,5岁那年,穿着开裆裤的他,见父母一脸汗水跑回家,竟不声不响爬上厨房灶台,盛了一碗粥捧给父亲说:
“爸爸,我长大了要给你和妈妈更好的东西吃。”
马建夫见状,当即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进了碗里。
父母眼里的“好孩子”马加爵,很快成了村里左邻右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他成绩优异,且很讲礼貌,小小年纪就懂得尊老爱幼。
在与马加爵家仅一墙之隔的村民马华成眼里:马加爵还是个讲信用的孩子。他一直记得:马加爵7岁那年,曾来他家借过一把螺丝刀的小马加爵,竟客客气气地给自己还了一把新螺丝刀。
后来的马华成才知道,还来的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旧的被马加爵不小心弄丢了,四处找不到,他就用父母给的零花钱步行十多公里到集镇买了一把……
在“懂事”、“好孩子”的赞誉声中,马加爵还抱回一张张奖状,马加爵父母欣慰不已。和当时的很多父母一样,他们多少觉得:孩子只要成绩好,就啥都好。至于孩子的心理,他们从未考虑过。
马加爵从小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孤独地、静静地坐着,母亲见了并不以为然,她甚至还觉得他这样“很省事”。
童年,总是无忧无虑,马加爵的童年也有很多欢乐时光,那时候他也没那么多课业,用来“玩儿”的时间自然也就多了。
童年时,与马加爵年纪相差不大的二姐经常和他一起玩儿,她的存在,也为他的童年增添了一抹亮色。
马加爵少年
“理想”这个美好的字眼,也是在这时候被植入了马加爵的心里。没人知道他何时有了做科学家的理想,但他树立这个理想时,状态一定是不错的。是啊,人只有在感觉良好的状态下,才会想到类似于“理想”等等的美好意象。
马加爵从未和父母提及过他的“理想”,父母很少和他聊天,他们的相处模式缺乏“流动性”。马建夫最看重儿子的成绩,至于其他诸如人际关系、心理等等,都不在他的考量范围内。他和同时代的多数父母一样,两只眼睛紧紧盯在他的考试分数上。
根据马加爵堂兄马加诚后来的讲述:马加爵和父母的沟通很少,反而和他的十四叔沟通更多。
马加爵的十四叔是马氏家族里文化层次略高的一位,马加爵动不动就拿“全年级第一”的喜人成绩,让十四叔对他刮目相看。
可颇让人遗憾的是:他的关注点也更多在考分上。
直到案发后,翻看儿子马加爵的日记时,他的父母才惊觉:少年时,他的心理就有些问题了。
马加爵的有一页日记里写上了三个大大的“恨”,这个“恨”的对象是他的祖母,而他恨祖母的原因,竟仅仅因为:一次看电视时,他要看动画片,奶奶要看戏剧,奶孙俩因此发生了争执。
更让马加爵父母惊讶的一页日记,写于他15岁那年。根据日记内容,当日的父母发生了争吵,为了帮弱势母亲“复仇”,他想将父亲从人间“蒸发”。“如果杀死父亲,要判10年刑,这样刑满释放时我就25岁了,不划算。”马加爵一“算账”,因“不划算”而放了父亲一马。
马加爵“杀父”的那页日记被写就时,他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按理,这个阶段的孩子最需要父母给予关爱和适当引导,可他的父母却依旧将目光放在他的考试分数上。
马加爵父母
在马加爵父母眼里:孩子是个“优等生”、“好孩子”,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全年级第一。他们一直记得:当时马二村有三个姓马的在班上,且成绩都不错。后来,学校还将他们“仨马”称作“三驾马车”,并作为典型在学校宣传。
成绩优异的马加爵在学校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优待,学校对于“学霸”总是格外爱护,如此一来,他在心理上即便存在问题,也完全没人理会。他的不合群,在同学眼里,甚至成了“个性”。
马加爵的奖状
1997年,马加爵考入广西16所重点高中之一的宾阳中学,高一时,他在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过二等奖。
马加爵靠成绩得来的荣誉,已不能让他兴奋起来,更多的时候,他体会到的都是学习的辛苦。有时候,他会疑惑:拼命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正是在高中时期,马加爵有了最本能的性冲动,他有暗恋的女孩,可他从不和人说。青春总伴着自恋,马加爵的自恋更加明显,自恋和自负往往一体,他在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姑娘”的同时,也忧心一旦她知道自己喜欢她,会给他难堪。
整个高中,马加爵都在重复枯燥的学习、复习、考试,他有些喘不过气。他的感觉非常不好,可他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因为:自始至终,他的世界里似乎一直只有学习,而没有真正的生活。
更加可怕的是,马加爵并不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如此一来,他遇到任何事,都只能自己一个人“硬扛”。
临近高考时,马加爵做了一件非常出格的事:他瞒着学校和家长,同社会上的朋友跑到离宾阳100多公里的贵港市去玩了。直到几天后,被当地民警找到,这场因他而起的风波才止息。
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跑去“贵港”,是因为他以为贵港的“港”是海港。没错,他只是想去看看大海,而已。
马加爵不管不顾奔赴“大海”的举动,是他内心极度渴望寻找美好的一个表现,也是他内心孤独的体现。或许,没有朋友且压力大的马加爵仅仅是想跑到海边放空,对着大海默默“倾诉”?
事发后,没有人留意到他的心理,老师和家长仅认为马加爵“纪律性太差”。
学校给了他纪律处分,考虑到他上高中不容易,又已到考大学的关键时刻,没有开除他的学籍。经历这次事件后,马加爵的心里更加迷茫了,昔日的理想不在不说,他心里还种下了一颗叛逆的种子。
颇让人费解的是,发生这么大的事,他的父母却并未责备他,他们当时想:先让孩子考试,考试最重要,考完了再说。
纠正孩子错误的最佳时机,从来只有一个,就是:他正在犯错或者错误刚被发现时。马加爵父母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可为了“考试”这个“大局”,他们选择了“暂时不理”。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加爵更加努力了,他开始日夜苦读,以考入理想的大学。马加爵的高考成绩很出色,按照成绩他可以报考哈工大,为了保险,他报考了云南大学。
见他考上了重点大学,马加爵父母决定不再追究他出走的事,他们想:反正都过去了,也没影响考试成绩。
到此时,“好成绩”依旧是马加爵各种问题的“保护墙”。
考上大学报到那天,父母借了6000元学费,亲自将他送到了云南。返回时,夫妇俩买完硬座火车票后已身无分文。
父母转身离开那刻,马加爵在校门前的天桥上,看着他们苍老的背影流泪了。在随后写给父母的信里,他表示要“发奋努力”,毕业后“还要挣钱报答双亲”。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马加爵很少开口向父母要生活费。马加爵父母后来在采访中说:“整个大学,他们只给了他1000多元。”
因为钱不多,马加爵必须在上学的同时努力养活自己。他开始打苦工,除了2001年春节回过家一次,每年的暑假和寒假他留在昆明打工挣点钱。
打零工挣钱对学生而言何其艰难,收入又何其低微。每次食堂开饭时,为了不让人察觉他的拮据,他总是最后一个就餐。他想:“这样,就没人知道我饭盒里没有鱼肉,没人会看到我的寒酸了。”
可买饭可以最后一个,穿着打扮却没办法“隐藏”。
无论冬夏,马加爵都常穿拖鞋出入,衣服更是一成不变。看到同学们一个个穿得光鲜亮丽,本就因生活艰难而“感觉很不好”的他,更加自卑、更加难受了。
马加爵
大学生活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相比初中、高中时期,他有了更多课余时间,这也意味着,他和同学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多起来了。他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马加爵发现自己无法融入同学中,其貌不扬、不善言辞,无形中给他的社交提供了障碍。看着大家都是三五成群,他却形单影只,他心里难免不好受。
孤独的马加爵在无奈中给堂兄写信求助,他问得非常直接:“我该如何与老师、同学们相处呢?”
如马加爵这般自负的人来说,他能写信向堂兄求助,已属于难得。他迫切希望堂兄能帮他融入集体,堂兄很快回信,堂兄鼓励他“大胆地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不要自卑和害羞”。
有了堂兄鼓励的马加爵决定主动融入同学中,可他“走出自我”的第一步,居然不是和同学们沟通,而是去尝试“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
多年不和人沟通的他,固执地认为:只要自己看起来很厉害,就可以吸引同学们的注意,甚至因此交到朋友。
马加爵一年四季洗凉水澡,这在学校几乎是“独一无二”,他自己也以此为傲。他的身体结实,胸前的肌肉尤其发达,为了表现自己的这一“厉害”,他特意站在澡堂外,让人给他拍照。
拍照时,他紧握右拳、努力隆起肌肉、瞪圆双眼,还做着一些自认为很酷的表情。因为用力过猛,他的手背青筋暴出,脸上表情也有些扭曲,整个状态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马加爵
显然,马加爵的澡堂表演,无法吸引到同学们的注意。这样的结果,让他很有“挫败感”。
马加爵并不气馁,他决定调整策略,既然“硬汉”不能吸引同学,那就换成“温柔攻势”试试吧!可怎么和同学展开“温柔攻势”呢,马加爵想到的是微笑+问好。
很快,马加爵就开始行动了,他一见到女孩就主动上前微笑着打招呼问好。有一天傍晚,他在楼梯口遇到一位女生,热情地叫了一声“晚上好”,那位女生抬头看了他一眼,“哦”了一声,便逃也似地冲下楼,这结果,让马加爵心里很不是滋味。
马加爵意识到:自己的温柔攻势,也不奏效。
在这之后不久,马加爵又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讲笑话。他想:幽默是人人都无法拒绝的,幽默的人最有魅力。
为了展现幽默,马加爵特地看了很多笑话,他还将这些笑话背下来了。准备充分后,他决心发动“幽默攻势”。
马加爵开始往人堆里钻,哪里热闹,他就往哪里钻,他想赢得一次表现机会。一次,一帮同学聚在一起讲笑话,他先是跟着大家一起“嘿嘿”笑,后来,他干脆着急地要求讲笑话。
因为长期不与人沟通,且本身没有语言天赋,马加爵讲笑话时显得笨嘴笨舌,他的笑话没有引人发笑,他笨嘴笨舌的样子却逗笑了同学们。表演结果完全出乎意料,马加爵懊丧的同时,感觉自己受到了嘲弄。
也从那时起,马加爵有了轻微“社交恐惧”,他见到人就躲得远远的,看到人围在一起说话, 他就觉得他们是在讥笑、嘲讽他。
马加爵并不知道:交到朋友的前提,是走出自我,去到对方。而“去到对方”的方式,则非常多,包括了解和谈论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帮助对方解决问题等等。他一直局限在“自我”,他自然只能找到通过“表现自己”来获取朋友的方式。
马加爵
封闭,是马加爵最大的问题。也因为过分封闭,他的心理渐渐出了问题,可在世纪初,心理学尚不成熟的年月,极少有人察觉到他的心理问题。
随着封闭的加深,马加爵的行为出现异常,他变得非常暴躁,即便是打球时别人不小心碰到他,他也会翻脸骂人。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愿意和他一起打球了。
马加爵总觉得别人会嘲笑他,甚至害他,为了自保,他拼命锻炼肌肉,还将头发特意剃成很短的寸头,以让自己看起来“更凶狠”。他不再主动与人交流,他唯一的“社交”是和宿舍的人打打牌。
后来,马加爵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被问到“学校有没有开心理辅导课”时,他的回答是:
“没有。听说有心理咨询机构,我没去过,没听说谁去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加爵的怨念越来越深,可他无从排解,他的感觉越来越不好了。人在感觉非常差劲时,是无法憧憬美好的,此时的马加爵,不仅再也想不到“理想”这个词汇,还连活着的意义都找不到了。
一个人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可怕在于:他随时会陷入琐碎小事之中,斤斤计较。
2004年2月初,寒假还未结束。马加爵所住的云南大学鼎鑫生活园区6栋317宿舍,十人间,住着七个学生。闲来没事时,他们常聚在一起“斗地主”。
317宿舍
一次打牌时,一位叫邵瑞杰的同学因怀疑马加爵出牌作弊,与他争执。争执中,邵瑞杰脱口道:“没想到连打牌你都玩假,你为人太差了,难怪龚博过生日都不请你⋯⋯”
因近段常与邵瑞杰一起打牌,马加爵早已在心里把他当成了好友。听到他这样说自己,他立马在心里恨上了他和龚博。
普通同学间遇到纠纷,顶多互相吵一架,或者找人倾诉一番,这事就算过去了。说白了,也就是几句话的事。可当时的马加爵已陷入了极度自我中,他不断在心里重复和邵瑞杰争执的画面,以及他的那句刺耳话。
仇恨渐渐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动了杀死邵瑞杰和龚博的念头。为了实施他的杀人计划,马加爵在网上查阅了许多资料,最后确定用杀人后流血相对较少的锤作为作案工具。
马加爵总是“想到就做到”,他迅速去旧货市场买了买石工锤,并让老板把过长的木柄锯短后带回宿舍。查阅了大量资料的他,还买了用于捆扎尸体的黑色塑料袋、胶带纸。
马加爵还将杀人以后出逃的步骤也想好,并去制证窝点制作了假身份证。但出逃以后又该如何,他并没有想好。
全程,已被仇恨笼罩的马加爵完全没想过父母、亲人。
正式杀人时,马加爵发现暂住马加爵所在317宿舍的唐学李成了他杀邵瑞杰的最大障碍。于是,2月13日晚,他趁唐学李不备,用石工锤砸向唐学李的头部。将其砸死后,用塑料袋扎住唐学李的头部藏进衣柜锁好,并认真处理好现场。
14日晚,邵瑞杰上网回来晚了,隔壁宿舍的同学已经休息,他只得回到了317室住。就在邵瑞杰洗脚的时候,马加爵用石工锤将邵瑞杰砸死。
这期间,马加爵有恐惧吗?没有!一个被仇恨装满的人,是不会有恐惧的。15日中午,马加爵正在宿舍处理邵瑞杰留下的血迹时,一个叫杨开宏的学生来317找马加爵打牌。杀红了眼的他,干脆用同样的方式了结了杨开宏。
就在当晚,已经完全进入癫狂状态的马加爵找到龚博,谎称“三缺一”。当晚,毫无防备的龚博也惨遭毒手。
马加爵刚处理完龚博的尸体,一位叫林风的学生也来喊马加爵打牌。因为觉得林风对自己不错,他没有开门。林风也因此逃过一劫。
冷静处理完现场后,马加爵拿着假身份证出逃。
云南大学的凶案惊动了中央领导,当年2月24日,云南省公安厅发布A级通缉令。
马加爵被抓捕归案时,已是3月15日。民警发现他时,已逃到海南三亚的他,正从垃圾箱里捡别人丢弃的剩饭吃。见到民警后,马加爵神色慌张,吃了多半的玉米棒子差点掉在地上。
而在看守所里,马加爵害怕得双腿发软,只得由民警架着他走出看守所。从监舍到看守所大门的几十米路,马加爵走了有四分钟。
正是在看守所里,自知难逃一死的马加爵写下了遗书。遗书却并非写给父母,而是写给他的十四叔、十四婶。他在开头第一句写道:
“十四叔、十四婶,你们好,我是在海南省三亚市看守所写的这封信。发生这种事情,肯定给整个大家庭带来了很坏的影响,但是对不起的话我再也讲不出来了。”
此时的马加爵和杀人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让他不一样的,正是他逃亡这一路的经历。逃亡路上,他所接触都是流浪汉或者残疾人,他的吃住也与他们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他终于开始冷静思考。
也因此,当后来被问到“你觉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时,他的答案是:
“活着的价值为自己是有的,但应该更多地为别人。以前没去想过这些问题,现在意识到了。”
可惜,一切都为时已晚。
马加爵的遗书很长,可通读全信后,世人惊讶地发现:他能回忆起来的人生最难忘的事情,仅仅是童年的一些碎片而已。马加爵自己也不知道为何会如此,但明眼人都知道:往后的岁月,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学习、考试。唯一不同的大学,他也一直在孤独中痛苦着,如此,他又有什么可写的呢?
马加爵并未给父母留遗书,他甚至在给十四叔的遗书里明确表示:自己不想再见父母。至于原因,他也说了,他说:
“代我劝我的父亲母亲不要再理我的事了,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们二人。因为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我真的变了很多很多,一个人从思想上变坏是不可救药的了。”
马加爵坚持不上诉,当被问及原因时,他说:“我也想惩罚我自己。”
怎样的人,会想要惩罚自己呢?答案是:真的觉得自己有罪的人。马加爵在行刑前的最后谈话中,没有提及“后悔”二字,但他的很多话里,却已然在忏悔。
提到案发时的种种,人问他:“如果那时候有人帮你一把,听你说话,倾诉倾诉,那天的事会避免吗?”他点头答:
“如果那样,我想后来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吵完架散伙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没人发现我情绪不好,我找不到人去说话。”
在给十四叔的信里,马加爵强调自己“从不迷信”,可在行刑前被问到“如果有来生,当如何”时,他很认真地想了很久,并给了答复,他说: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献身科学的人,专门搞学问。希望不要那么冲动,有什么事可以向别人说说。”
马加爵的老家,有一幅他收藏的水墨,上面有一个特大号的“忍”字。这幅画表明:他在很早以前,就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心理有一定问题。这幅画,甚至可以被看做他施行“自救”的方式之一,可惜,他并未奏效。此后的无数年里,他也一直未找到理性、正确的方式拯救自己。
逃亡时的马加爵
生存还是毁灭?马加爵选择了后者,他的选择伤害了四个无辜的生命、摧毁了四个家庭的幸福,他可恨,却也可怜。
愿类似的悲剧,不再上演!
这些回复亮了

style1975
· 安徽那个采访说的比较含蓄,几个因素,马加爵:没有女朋友,但有过性行为,在校外。

Timo13
· 上海嫖虫都觉得别人和你一样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