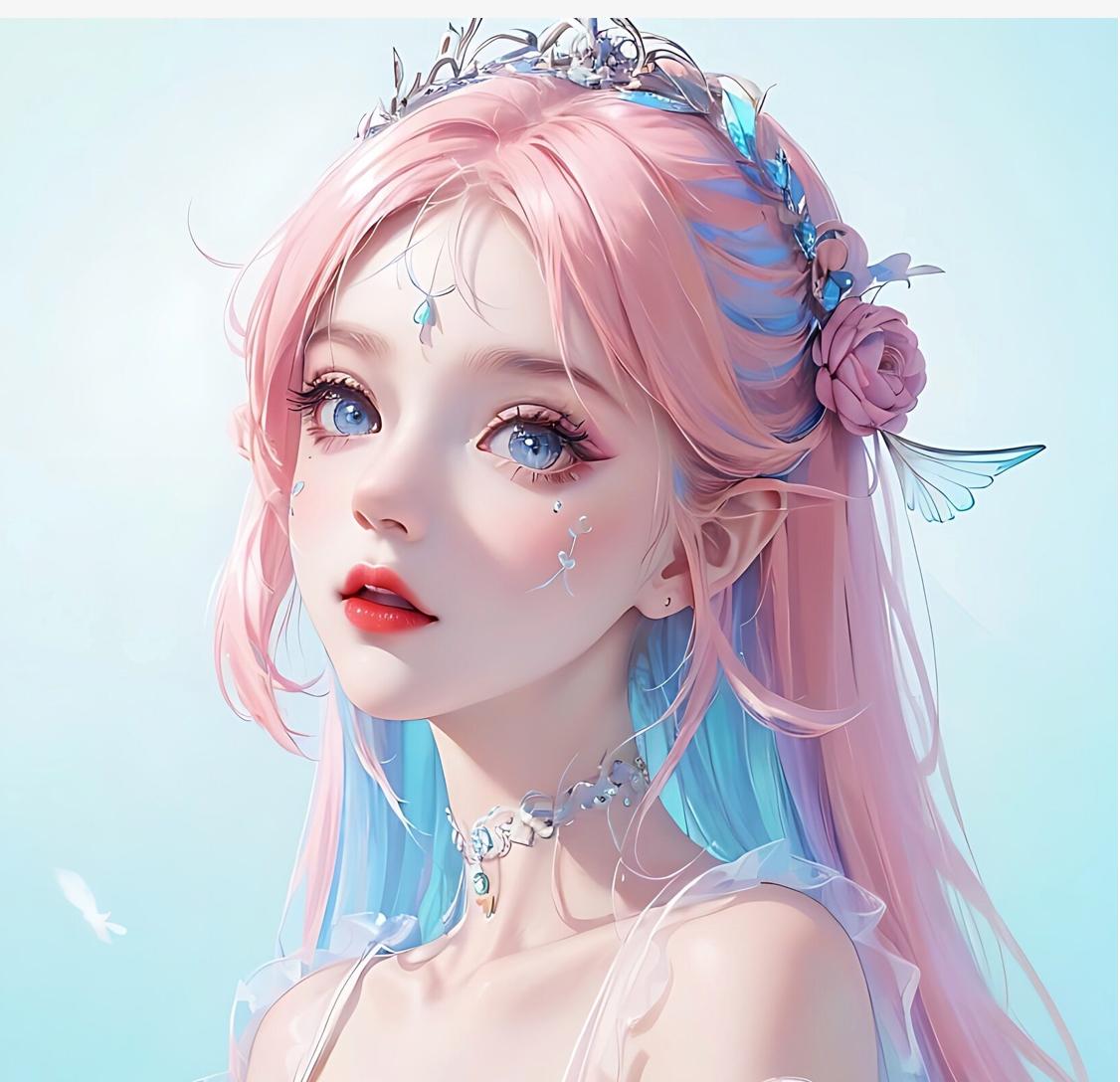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如果没有莞莞类卿事件,甄嬛和雍正结局会改变吗?
我入宫是七月初一,那天永乐宫死了位贵人。
抬棺椁出去时,正从我身边过。
说是姓冯,一个从七品县令的长女,生得盘靓条顺,养得能歌善舞,刚入宫时也曾讨过半月恩宠,从常在一路升上来,不是没有得意之时。只是偏偏后来不长眼,惹了不该惹的荣昭仪娘娘,七天前被叫去了承欢殿,再抬出来便是今日,活蹦乱跳的美人变成了一个死人,还是一具恶臭熏天的腐尸,叫永巷来来往往的人避之若浼。
关于这七天发生了什么,有人讳莫如深,也有人议论纷纷。最为人称道的说法是,风头正盛的荣昭仪把冯贵人扔进了一口枯井,备了两框石头,一块一块地掷下去。那井里先是求饶,再是咒骂,然后一声声惨叫不绝于耳,到最后惨叫声也越来越小,提着一口气的冯贵人在井里整整呻吟了两日半,身上的腐肉都生出蛆虫,最后才断了气。
多大仇才至于这一出啊?
引鸢替我问出了这困惑,得到那群唧唧喳喳小宫女的回应,说是荣昭仪赏了小跟班纪容华一双妆花缎面的鞋,纪容华定省给仪贵妃请安时,被冯贵人踩了一脚。这小跟班表面不动声色,背地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跪在荣昭仪面前,先说自己连一双鞋都护不住真该死,又说冯贵人故意当着仪贵妃的面糟蹋荣昭仪赐给自己的物什,是摆明了打荣昭仪脸。
结果这一脚,再加上纪容华一通哭,生生要了冯贵人的命。
引鸢还想和她们扯上几句,就先被我拖了走:「别误了见过贵妃的时辰。」
引鸢心里的不乐意窜上微蹙的眉梢,她是分给我的侍女,也是宫里顶瞧不上我的人。
不只因为她曾给去世的皇贵妃打过洗脚水,看不上我一个区区答应,也是因为见她第一面,我就问她:「这宫里,有嫁过人的女人么?」
她那时的不屑还穿上了一层恭敬的伪装:「当然了,宫里的娘娘们,都是嫁了皇上的女人。」
「我是说,在进宫前,就嫁给过别人。」
引鸢愣住了。
「我就是这样的女人。」我露出一个真诚的笑。
从小我娘就说我,我这人有一个顶大的毛病,就是过于坦诚,有一说一,不会藏着掩着,也不会兜兜圈子。
可是坦诚有什么不好呢,提早告诉引鸢这番事故,断了她对我一岁九迁共享荣华的念头,总好过死心塌地跟着我多年,发现我表里如一,真是个扶不上墙的阿斗要好。
引鸢接受了我的坦诚,自此把瞧不上我四个大字高高挂在脸上。
给一个嫁过人的末等答应做掌事宫女大概是她平生最丢人也最心塞的事情,痛苦而没有希望的生活让引鸢唯一的人生趣味变成了怼我,没事唱个反调摆个脸,她心里乐呵些,我也感觉没那么惭愧。
七月初三,入宫第三天,我拜见了各位娘娘,活在传说中手段残酷不可一世的荣昭仪却并未露脸。
宫里位分最高的仪贵妃端庄地位于上座,像尊镶满了宝玉的菩萨像,雍容华贵彝鼎圭璋都不足以形容其冠绝四方的气场。两侧是紧随其后的婉妃与庄妃,再后面跟着柔充仪、慎嫔、僖嫔、康嫔,往后还有几位婕妤、容华、贵人,都没了封号。再往后的,便连坐着的资格也没了,是在这后宫中排不上名的美人、常在、答应、更衣。一群环肥燕瘦几十号人,莺莺燕燕挤满了一个大殿。
而我,就是最末等的答应。之所以没被册为更衣,是因为我没有资格,一般都得犯了大错的娘娘们才能被贬到更衣,我要再被贬,就只能进冷宫了。
仪贵妃受了我的参拜,指给我各位娘娘让我一一行礼,又教育了几句,行了封赏,便让我退到妃嫔的末流立着,她们煞有介事地议起了正事。
所谓正事,也就是背地里嚼嚼舌根子。
一张谄媚脸的康嫔幽幽地说了几句荣昭仪的坏话,正说着她定是知道自己做的好事,躲自个儿巢里等着被打入冷宫的旨意时,门外当真来了张旨意。
只不过送旨的卫公公读完明黄卷轴上的寥寥几句后,这屋里一半女人绿了脸,另一半女人倒吸一口气,只有我,闪烁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贼眉鼠眼。
那道旨,说要晋封荣昭仪为荣妃,还一跃老资历的庄妃婉妃,成为众妃之首,仅居仪贵妃之下。
打死个人,升了位分,真是吃了人还吐出骨头被夸吃得好的后宫。
我吓了个哆嗦。
回去后,为了让热爱八卦的引鸢开心一点,我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她。
「贵人,你说贵人是不是大我好多呀。」我扳着手指一级一级算起来,「那昭仪不是大我更多,我记得皇上的生母,先皇的嫔妃,到死也不过封了个嫔位。」
引鸢不屑地冲我翻了个眼,又拿出前皇贵妃身边打洗脚水宫女的高傲嘴脸:「您还真敢拿自己个儿比啊,毓秀宫的王美人今儿见了么,入宫七年了,刚进宫是个常在,这么些年也就升过一级,都没做成贵人。您啊,年纪长,入宫前又……是吧,又与众不同,您能熬到个美人,就是我们合宫积福了。」
我们合宫只有我和引鸢两个人,也刚刚就她的福加上我的福,怕也不够福泽深厚。
「那你说荣昭仪,哦不对,荣妃,弄死了人,她心里不怕么?」
「怕?呵!」引鸢捋了把袖子,插着腰,俨然一副要讲故事的样子,「她要是知道怕字,皇贵妃娘娘也不会死。」
我再往后问,引鸢就钳口不言了。
她是个嘴上没门的人,但是心里却装了把锁,心里打定主意不说的事儿,就算从嘴边窜了出来,也只是拼凑不出信息的只言片语。
七月初七,乞巧节,传说中有情人的鹊桥佳期,皇上来了我宫里。
那时我站在窗边,盯着半轮层云后影影绰绰的残月。
他问我:「你看什么?」
我说:「除了月亮,还能瞅啥?」
他沉默半晌,走过来拉我的手,亦步亦趋,让我依着他走入了红绡软帐。
我们说了些话,却没做什么事。子时未至,他便走了,合服工整,我也是。
推门而出时,在门外侍奉的卫公公和引鸢似乎都看出了些什么。卫公公意味深长地往里探了一眼,引鸢送走皇上便兀自入内,帮我理了理丝毫不乱的衣领,恨铁不成钢地说了句:「主子还是早些歇息吧。」
人都散去之后,我又回到床边,摸了把椅子坐下,继续对着那轮月亮。
我看着云飘来散去,一个时辰过去了,我也看不出它有变圆的趋势,怎么等到七月十五那日,就生得浑圆了呢?就好像我,日复一日对着镜子,从未觉得自己比昨天老了些,却真真切切过了七度春秋,从二八少女到花信之年。
我想起十六岁初次嫁人,想起也曾郎情妾意相濡以沫,想起与那人算不上和离的别过,想起后来家道中落被送入寺中一晃便是七年,直到上个月,当朝圣上李承穆摆驾安元寺,在后山对我一指。
——「把她送宫里吧。」
第二日一早,我去给仪贵妃请安时,同屋的冯婕妤和康嫔窃窃私语,一边看着我不屑地嬉笑。仪贵妃斥了她们两句,挺着高傲的胸膛,昂着高贵的头颅,目光自上而下投射在我头顶,仪态万千地开口抚慰到:「皇上近日忙于朝政,在你那只流连片刻,冷落了你,你要体谅。」
得勒,这后宫真是有趣,好事出门,坏事也出门。得了宠招人恨,不被待见也招人嘲。
一连几日,我走路上都有人指指点点。就连一向瞧不上人,连我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的荣妃,也终于把我放进了眼皮子里,在清晔池旁遇着我,掩唇失笑道:「这不是第一次侍寝就把皇上吓出来的什么答应么,来来,快让本宫好生瞧瞧。」她说着还伸手勾我下巴,「这模样也没多下作啊,怎么就吓到了皇上呢?哦,年纪瞅着倒是长了些。」
她像把玩一块玉石一样端详着我,还拉了把身边小宫女的衣袖:「哎呀你说咱们这位皇上也真是,宫里难道还缺容颜老去的半老徐娘么?何苦讨人家进来,又嫌弃人家?」
这话听上去,好像就她和皇上熟似的,放肆有时只是种炫耀吧。
回去后我问引鸢,皇上半夜离开我这儿,真的是这么值得说道的事儿么?
引鸢点点头,看着我一脸困惑又摇摇头,最后给我倒了杯茶:「主子,多喝点热水吧,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
在引鸢眼里,我扶不上墙阿斗的形象真是洗无可洗。
这一切的转机来源于七月十五的中元节。
据说七月初七之后,皇上就没踏进过后宫。
往年的中元节,皇上都要外出,在皇家的昭仁寺中守着先皇和容和太后的灵位,或者是在宫中的佛堂内拜祭一宿。这一夜,宫里的女人们也没指望能蒙上皇上恩宠,何况民间也说,鬼节里行男女之事颇有不吉。
我从小就怕鬼,幼时这种日子里都会钻进我娘的被窝,在寺里那些年,也要在和尚们念经的偏殿躲上一宿。
而今晚,我只有引鸢了。看着她一副爱答不理,以及不能理解一个二十五岁女人还怕鬼的眼神,我第一次冲她投去了恨铁不成钢的目光。
子时将至,就在我准备灭了烛火,龟缩床上闷头一晚时,皇上来了。
卫公公没在门口喊场面话,于是他悄无声息就进来了,然后灭了烛火,抱住我,我的下巴抵上了他的胸膛......
第二天,后宫里又炸了。
我走在路上依旧被人指指点点,只不过冯婕妤的不屑变成了厌恶,康嫔的嘲讽变成了不甘。
我是一个中元节有皇上陪了一宿的答应。
只不过一个月过去了,我还是答应。
我自在地过着,引鸢却不时地长吁短叹,无非是些怎么还没有晋封的旨意,连恩赏都没怎么赐过的抱怨。
我看着她突然燃起了斗志与希望的模样觉着好笑,一点都没了之前心如死灰时的稳重。不过也许之前的也不是稳重,只是对我的绝望。
我把皇上前些日子丢在这的玉佩抛给她:「这不是也有些恩赏么,给你了。」
她惑然:「什么时候派什么人赐的,我怎么都不知道。」
「就前两日,皇上早朝前,从腰间解下来搁这的。」
「妈呀!」本来还小心赏玩着的引鸢像丢烫手山芋似的扔回我怀里,「这我怎么敢要?皇上贴身的东西,这可是天大的恩典啊!咱们这位皇上我真是看不明白,既然看重主子,怎么就让主子做末等答应呢?」
「你之前不还说,我们合宫积福混个常在就不错了。」
「那是那会儿。」引鸢摆摆手,「那时候谁知道您,是吧……虽然前科累累,但却能引得皇上频繁光顾啊。一共来五次后宫,四次是看您,还有一回是承欢殿那位不好惹的荣妃娘娘非把皇上请了去,后来大半夜的,皇上还走了。」
是了,听宫里人说,但凡有新人承宠的,哪怕只两三次,也定要被荣妃打压到再不敢抬头看天,直把荣妃当这后宫里的天。到我这倒是奇了,荣妃一次也没刁难过我,想来是和我有了一样皇上来了又走的境遇,这才生了同病相怜之情。
然而听到我这论点,引鸢只有继续恨铁不成钢啐上一口:「得了吧您嘞,还同病相怜,荣妃只是想起嘲讽您那次,脸上有些挂不住。您也先别美,这位主儿手段辣着呢,她能放过谁呀,厉害的在后面等着您呢。」
厉害的等着我她美啥,还说得绘声绘色口若悬河的,我真不明白。
八月初九,中元节后皇上第六次来了后宫。
自我承宠以来不满一月,仪贵妃表面功夫一向做得好,从不为难我,也从不亲近我,没亏待过我生活,也没多赏过我物什。荣妃那边不作妖,庄妃一向不惹事,婉妃是个病秧子,柔充仪失宠了好一阵,高位的这几位娘娘不表态,下面的人苦荣妃久矣,我一个区区答应既翻不起浪,又能气气荣妃,大家也就当看个热闹,心里爽一把便算了。
反正按照宫里一贯的规律,没人真能承平日久,何况我依旧只是末等答应,位分上谁都能踩上我一脚。
这一日皇上喝了点酒来的,一进屋就揽我腰,引鸢还在呢,他就旁若无人把我搁他腿上坐着,嘴里念叨了几句朝政又说了几句胡话,突然把脑袋埋在我颈脖之间,浓情蜜意唤了声:「毓儿……」
我傻了,引鸢也傻了。只不过这个坏胚子犯傻的方式就是脚上抹油溜之大吉,把我一个人丢在皇上的怀里。
他以为我的僵硬是无动于衷,于是把我搂得更紧,嘴里一声接着一声喊:「毓儿,朕的毓儿,这么些年苦了你……乖毓儿,再不要离开朕了,你心里苦朕都知道,朕也苦,朕没有一天真能忘了你……」
毓儿……
想我……
苦……
这些字眼在我耳边不断回旋,搅和着他沉重的鼻息,他裹挟的酒气,不断地刺激着我,直到我终于受不住,蓦地站起身,蛮横地推开他疲软而尊贵的身子。
「我不是毓儿!」我冲他大声喊道。
「毓儿?」他眯起惺忪的眼,为了把我看得更真切。
「我不是毓儿!」我的声音又高了几度,我不知道自己失态了,我只知道自己很拼命,拼命地向他阐述着一个事实,「我是长宁,叶长宁,你从安元寺接进宫的叶答应!我不是毓儿!」
他一下子停住了醉酒人不可自持的摇摇晃晃,敲了敲自己脑袋,又抬起头盯着我,最后偏执地小心翼翼地继续试探:「毓儿?」
我累了,长叹一口气,跑到窗边让夜风灌进来:「你醒一醒,我不是毓儿!」
他坐在那,和我僵了良久,最后不知是真的醒了,还是他也累了。
「朕明白了。」他说,然后艰难地撑起摇摇晃晃的身子,挪到门边。
他走了。
没看到他想看的毓儿,他走了。
他走后,引鸢和那次一样,走进来帮我理了理衣领,没等她让我早些歇息,我先一把拉住她的手:「陪我坐会吧。」
引鸢难得地和我说了很多事情,而不是怼我。我猜她真的觉得我可怜了,人同情另一个人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多带些善意和信任。虽然引鸢自己说的是,我们现在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我若就此失宠,她后半辈子也就陪着我无声无息,要不老死,要不被人搞死。
她告诉我,毓儿,是那位殁了的皇贵妃的乳名,她侍奉先皇贵妃时,遇着过几次皇上在,皇上就是这么叫她,毓儿毓儿,叫得一片痴心,无限柔情。
皇贵妃林氏,名已不可考了,乳名唤毓儿,出身不高,本来都入不了秀女殿选,可谁知皇上看了眼画像,就着了迷道一般非要选她入宫,一入宫便封了婕妤,这可是王宫贵胄家嫡出的小姐都够不着的待遇。
短短两年,连升四级封了贵妃,当时仪贵妃还是仪妃,身世高,资历老,名望好,却还是被这位林贵妃压在脚下动弹不得。皇上故意没赐贵妃封号,他说他的宫里就这一位贵妃,无人可比肩,也不需要封号做区分,生生断了仪妃庄妃云云的晋升之路。
不仅如此,前朝那般压力,皇上还是执意封林氏为皇贵妃,实际上那时的林氏已经和皇后没什么区别了,三千宠爱冠绝六宫。这位皇贵妃本身性子也温婉和顺,在后宫颇得人心,和皇上和和美美,羡煞旁人。
本以为这一生也就这样过了,等着生个皇子,封了太子,哪怕林氏出身再卑贱,母凭子贵,封后也是迟早的事。
直到荣妃江笑情入宫。
江笑情是皇上的表妹,皇上母家不算尊贵,这位荣妃自然出身也并不显赫,容貌也算不上一等一,只是生得活泼灵动,敢打敢闹,万种风情,再加上三分亲缘在,一入宫便分了皇贵妃不少宠爱,这在后宫还是从未有过的事。皇贵妃本来身子也不算好,这一下子就落了心病,虽说身子弱了,可谁知竟在这时候怀上了。皇上那高兴的呀,恨不得每天捧手心里,多一寸力都唯恐给捏碎了。可是,谁也没想到……
「没想到啥?」我推了把说书好手引鸢,「别在这种地方卡壳啊!」
「您还真当听书啊,我是想告诉您这宫中旧事,提点着您些。」
「那我可不真当……」看着她幽幽的面色,我咽了口唾沫,「真当受您提点呢。」
我左哄右哄,引鸢终于又恢复了绘声绘色。
宫里有个习俗,每年有几个特殊的日子,位分高的娘娘们是准许回去省亲的。本来怎么也轮不到入宫不久,也还只是个容华的江笑情,但她毕竟颇得圣宠,加上有沽名钓誉的仪妃求情,那年的二月二,皇贵妃就和江容华一同出了宫。
结果谁也没想到,回来之后,皇贵妃就自缢了,一尸两命。
「那二月二那天,她们去哪了?」
「知道的人都被逐出宫了。」引鸢叹了口气,「现在宫里知道的人,怕只有皇上了吧。」
引鸢说着慢慢转向我,将我左右端详,良久道:「我真傻,我第一眼就该看出来,您和皇贵妃样貌可真像,难怪皇上会宠您。可您今儿,您怎么就……哎……」
「你说,那位皇贵妃,和我像?」
「我是说,您和她像,您也真把自己当回事儿,还说她和您……」
引鸢后面絮叨的那些我都听不清了,我就是特别想知道她为什么要自杀,特别特别想。
后来我又追问了些,但是皇上都不想让人知道的事,引鸢又能知道几分呢。她能和我分享的,也仅有那些后宫里的人都看在眼里又不敢非议的事实。皇贵妃死后,摆明了和这事儿脱不了干系的江笑情,也仅仅是被禁足了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放出来,江笑情也换了个人似的,原本虽然颇承圣宠,也爱卖弄几番风情,却不是多么阴狠毒辣之人。这事儿出了之后,江笑情像是找到了人生乐趣,自此把为祸一方当成了奋斗目标。后宫里的人,但凡让她蒙了眼的,管是沙子还是沙尘暴,都要好好尝一尝江笑情的手段。贵人以下,掌嘴杖责罚跪都是家常便饭,哪怕是高居妃位,被江笑情以下犯上怼得哑口无言也是见惯不惯。
偏偏这样的江笑情更得圣宠,皇上对她的过分行径像是默许了一般,她闹得越出格,皇上就越给脸。虽难复当年皇贵妃,却也逼得六宫粉黛无颜色,两年不到就骑在了一众老人头上。原本还被皇上垂青过几日,家世甚好,资历也老的柔充仪自此是连皇上面都没怎么见到,生生被初生牛犊的江笑情压脖子上,再也没能直得起腰。
再后来,我就都看到了,荣昭仪活活打死冯贵人,却被封了妃,连一向位高权重的庄妃婉妃二位都被比了下去。
所以那年的二月二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两个女人的命数,还连累了一个尚未见过人世的胎儿。
我不知道,也怕真相过于血淋淋,不如等干涸了再去翻开得好。
自从在我这强叫毓儿不成,反碰了一鼻子灰后,皇上便再没来过。
对于我骤然得宠又倏然失宠的事儿,后宫里的人并未大惊小怪。据说自皇贵妃殁了,后宫里总有女人能得皇上流连一番,只是后来要不就惨折在荣妃江笑情手里,比如突然断了腿的刘美人,倒了嗓子的贺常在,脸上生了斑的殷贵人,要不就过几天便让皇上失了兴趣。仅有的几个爬得稍微高些的,也就一直对荣妃马首是瞻的僖嫔,还有对仪贵妃唯唯诺诺的冯婕妤了。蚍蜉难撼树,但换个思路,抱住了大树,偷生也不是坏事。
这些日子里,起初我还守规矩,每日卯时将至,便去给仪贵妃请安听训话。可自打有一日突然降温我实在没能起得来床,也发现没人发现我没去之后,我便从此心安理得地闭门不出,仪贵妃也从未差人来问责,日子一久,我便像被合宫忘记,淡出她们的谈资。
所谓有得必有失,这也害得我失去了每天听一群女人嚼舌根子的大好机会。然而,后宫怎么会缺爱叨叨的嘴呢,说书好手引鸢每次外出,只要流连的时间长了些,便定要带些八卦满载而归。
如今的宫里,我失宠了,风口浪尖的人又变回了荣妃和仪贵妃。
前朝近日来上书不断,纷纷奏请要封仪贵妃为皇贵妃,实实在在一统六宫之事。之所以不请封皇后,是因为皇上继位以来已经被奏请叨扰了数多年头,皇上实在态度坚决不立后,前朝也慢慢死了心。
要论家世,这后宫中最显赫的便是手握军权的兵部侯尚书和临平郡主家的嫡长女仪贵妃,还有太子少师海大人老来得的宝贝女儿柔充仪。
兵部尚书一出手,谁都不敢兜着走。也许是荣昭仪被封荣妃的事儿刺激到了这位侯大人,侯大人一呼百应,在朝堂之上递折子请皇上册立皇贵妃,变成了朝野之间风靡一时的流行指标。
皇上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搁下折子,一转身悄咪咪收了海大人送进宫的歌女,唱了两天歌,封了常在,甚至赐了本该嫔位以上才有的封号莺字。于是就在我销声匿迹的这几天,莺常在唱成了新宠。
柔充仪那头摆明了态度这是海家的人,荣妃也只得怼几句出出气,最后也没能拿这莺常在怎么办。
八月二十九,皇上有整整二十日没再来过。
引鸢长吁短叹,我躺在门外的摇椅上,晃着轻罗小扇,眯眼瞧着月亮,满是惬意。
是夜,西院隔着一堵墙的地方传来了萦萦绕绕的歌声。
引鸢啐上一口:「好不膈应人!不知是皇上的意思还是仪贵妃故意想恶心主子,竟将这莺常在安排在了咱们西边的玉暖阁住着。主子见不着皇上就算了,还得听着这歌女是怎么勾引皇上的……
👉点击继续阅读
全部回复

大学宿舍那点事
· 北京看看如懿传就知道了,结局不会变的
暂无更多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