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格雷格·波波维奇: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印第安纳州梅里尔维尔 —— 1967年那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敲门声总是准时响起。吉姆·弗米利恩几乎不用开门,就知道门外会是谁。
十有八九是18岁的格雷格·波波维奇。这位刚刚结束在空军学院第一年学习的年轻人,回到印第安纳州西北部的家乡,总是带着同样的请求。
“他说:‘教练,能不能让我进体育馆?’”弗米利恩回忆道。
作为梅里尔维尔高中的篮球和棒球队助理教练,同时也是波波维奇一年前的毕业校友,弗米利恩是少数几个握有钥匙的人之一。
他会带着这位年轻的追随者走进学校的体育馆,在那里,这位未来将带领马刺队赢得五次NBA总冠军的传奇教练,每天都用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不做的事情——令弗米利恩惊讶。
“你想啊,任何一个孩子进了体育馆会干什么?他一定会说:‘给我个篮球。’可格雷格不会。他能一个小时不碰球,只做防守滑步训练。这才叫投入。”弗米利恩说。
那个夏天,他们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这样的日常。第二年夏天依然如此,两人逐渐不再只是师生,而更像朋友。
(下图为老年Jim Vermillion)
几十年后,当这位昔日学生已声名显赫,成为NBA的标志性人物时,弗米利恩依然会回想起那些时光。那时候,波波维奇完全可能——甚至理所当然地——远离小镇的根脉,但事实并非如此。
2012年,弗米利恩结缡52年的妻子因渐冻症去世。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即便正值马刺队赛季,波波维奇也坚持每月打电话问候。直到生命的尽头,弗米利恩的妻子已无法开口,甚至无法动弹。
“可当我告诉她,是格雷格打来的电话时,她就会哭。”这位当年还曾教过波波维奇物理课的老人说,“她就是那么喜欢他。”
2025年5月2日,格雷格·波波维奇正式卸任主教练职位。马刺的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式结束。在漫长的29年里,波波维奇为马刺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五个总冠军,4位名人堂球员,1390场胜利,这些显而易见的功绩不足以概括波波维奇的意义。
这份彪炳战绩,已使波波维奇在圣安东尼奥享有近乎神祇般的地位。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依旧神秘而难以接近。
在全国的篮球迷眼中,他既因赛场上的智慧受到尊敬,也因场边采访时简短甚至带点戏谑的回答而闻名。
但在距离芝加哥市中心东南42英里的梅里尔维尔,人们认识的是另一个波波维奇。
“他就是个普通人。”梅里尔维尔高中的助理体育主管艾米·贝克汉姆说,“他从未忘记自己在印第安纳的根。”
体育与钢铁
1949年1月28日,波波维奇出生于印第安纳州东芝加哥市印第安纳港的工业区。他的父亲雷蒙德是塞尔维亚裔,母亲凯瑟琳是克罗地亚裔。
当时的这里,和现在一样,是篮球的热土。
孩提时代,波波维奇最初的梦想,是为传奇教练约翰尼·巴拉托效力——那正是他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作为明星前锋大放异彩的东芝加哥华盛顿高中。
那个幻想在波波维奇五年级结束后被打破了——他的父母分开了。母亲带着全家搬到南边18英里的梅里尔维尔,这是个被农田环绕的半乡村社区,当时人口还不到1万5千。
“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波波维奇在2001年接受《德州月刊》采访时回忆道,“我妈得拿扫帚把我赶出家门。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车库里,她跑出来拿着扫帚打我的头,把我踢到街上去,因为我就是不肯离开。”
“湖区”——这是密歇根湖南端一串小镇的俗称——曾经依靠繁荣的钢铁工业而兴盛。
1906年,美国钢铁公司在湖岸边建起了当时北美最大的联合钢铁厂。公司还修建了加里市(以美国钢铁联合创始人埃尔伯特·H·加里的名字命名),安置涌入的工人。
从20世纪初开始,加里钢铁厂及周边工厂的烟囱滚滚白烟吸引了大量求职者,其中不少是来自东欧的移民,他们让加里及周边的东芝加哥、梅里尔维尔、格里菲斯和皇冠岬等社区人口迅速膨胀。
父亲进厂,儿子也进厂,一份钢铁工的薪水几乎成了代代相传的“世袭”。
进厂是份好差事,薪水丰厚,还有养老金保障。
“我以前经常听高三的学生对我说:‘到明年这时候,我挣的钱就比你多了。’”现已退休的弗米利恩回忆说,“他们说得没错。”
波波维奇的母亲在内陆钢铁公司做秘书,继父鲁迪·海杜克则是那里的行政人员。
梅里尔维尔高中1966届的许多同学毕业后也走进了工厂。
“可他不想那样。”教了波波维奇两年数学的马克斯·哈钦森说,“他想上大学。”
1966年高中毕业后,波波维奇接受了空军学院的录取,成为梅里尔维尔历史上首批进入军校的学生之一。
但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在召唤他。
如果说钢铁把印第安纳西北部的居民紧密捆绑在一起,那么体育则是另一种凝聚力。没过多久,篮球就融入了波波维奇的血液。
“他有我们说的‘篮球瘾’。”自初中起就是他至交的阿利·皮尔斯说。
入选之路
在成为篮球世界里人尽皆知的“波波”之前,他的朋友们叫他“C.C.”。
这是因为梅里尔维尔高中的篮球教练比尔·梅特卡夫脾气火爆,总记不住他的名字,总是叫他“克雷格”。他的朋友们觉得好笑,就把这个错误的名字和他真实的中间名查尔斯拼在一起,给他起了个新外号:“C.C.”
“哦,他可讨厌死这个了。”皮尔斯说,“所以我们偏要叫。”
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等着他。1963年,高二的波波维奇被梅特卡夫从篮球队裁掉。那个曾梦想为东芝加哥华盛顿高中参议员队效力的少年,竟然在梅里尔维尔海盗队都没能站住脚。
但波波维奇没有退缩,反而更坚韧了。皮尔斯回忆说,第二天波波维奇拉上他,两人一起去了邻镇加里市39街与百老汇的户外球场打野球。
“就是在那里,他学会了坚强。”皮尔斯说。
当时的梅里尔维尔高中全是白人,而加里的比赛是融合性的。很多球员的父亲在钢厂干活,买不起篮球鞋。
“他们就穿着父亲的钢头靴。”皮尔斯说,“可他们还是能轻松过掉我们。我们就说:‘我们得变得更强。’”
夏天,波波维奇和朋友们会跑到附近格里菲斯镇,在一个叫“The Courts”的公园打高强度的比赛。那是中西部心脏地带的鲁克公园——各地高手云集,比赛艰苦,竞争激烈。
“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那里打球。”弗米利恩说。
等到高三重返试训时,梅特卡夫依旧叫他“克雷格”,但同时也让他成为海盗队的首发中锋。这大概是波波维奇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锲而不舍”。
“我很快就发现了格雷格的特质。”弗米利恩说,“你根本挡不住他。”
一尘不染
波波维奇在梅里尔维尔的成长很典型。
除了打篮球,他还在棒球队担任游击手,尽管表现并不总是理想。按照好友皮尔斯乐呵呵传播的“传奇”,波波维奇曾连续23次打击被三振出局。
不过他还是个优等生,深受老师和同学喜爱。
琼安·沃特金斯就住在卡罗莱纳街上,和波波维奇家正对门,经常和他的小妹黛比一起玩(如今黛比已是佛罗里达大学教授)。
“我总记得他在外面练篮球。”沃特金斯说,“他打体育,当然很受欢迎。”
自波波维奇的时代起,梅里尔维尔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它靠近65号和94号州际公路交汇处,遍布连锁餐馆和大型商场。
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小镇的青少年没多少娱乐活动。波波维奇和朋友们常常周末开车在百老汇兜风,或者去当地一家叫“Mug”的店里买14美分的汉堡,有时也会看露天电影。
朋友们说,波波维奇的家庭生活并不严格,但很有条理。
“家里从来没有一点灰尘。”皮尔斯说。他后来成了波波维奇婚礼的伴郎,如今仍在这位马刺主帅的核心朋友圈子里。“他妈妈每天都确保餐桌上有一顿像样的晚餐。”
或许这也预示了波波维奇日后另一大爱好——他的继父在梅里尔维尔的家里建了一个酒窖。不过皮尔斯坚称,波波维奇当时最爱的饮品可没那么高雅。
“我们都喝16盎司的斯特罗斯啤酒。”皮尔斯说。
夏日午后,他们有时会开车半小时去芝加哥,看厄尼·班克斯、罗恩·桑托和心爱的芝加哥小熊队在瑞格利球场比赛。1966年公牛队成立后,他们也偶尔去芝加哥体育馆,看杰里·斯隆和鲍勃·布泽尔那种强硬的打法。
马刺球员们若再遇到暂停时被波波维奇红着脸痛骂的场景,不妨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据朋友们回忆,波波维奇当年是摩城音乐的粉丝,还特别爱跳舞。
“他其实跳得挺好。”皮尔斯笑着说,“估计他要知道我告诉你这些,会把我宰了。”
即便如此,少年波波维奇的心思依旧离不开篮球。朋友们虽然也喜欢这项运动,但他却是彻底的痴迷。
同学们还记得他在学校走廊里绑着脚踝负重锻炼腿力。放学铃一响,他就急急忙忙去找球打。
“他有种一般孩子没有的驱动力。”弗米利恩说。
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这种不同寻常。
正是这种驱动力,把波波维奇从印第安纳西北角带到空军学院。
壮志凌云
1966年秋天,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空军学院体育馆里,汉克·伊根正担任鲍勃·斯皮尔的助理教练。就在那时,刚刚从印第安纳州梅里尔维尔高中毕业几个月的波波维奇,和一群新学员一起走进了球馆。
“我们当时正想弄清楚谁能做什么。”伊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他很有冲劲。”
这位“锈带”出身的年轻人高二时曾被高中球队裁掉,但在高四时却带领梅里尔维尔海盗队成为得分王(场均15分),并被评为印第安纳州西北部卡鲁梅特联盟全明星。
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既是演讲与辩论队、学生会和国家荣誉协会的成员,也在篮球、棒球和越野项目中赢得校队奖章。
在空军学院,伊根立刻看出了波波维奇的聪慧、好胜与上进心。
波波维奇在大学最后两个赛季都进入了一队,并在大四担任队长。在那段时间里,他和汉克·伊根经常谈起未来——即便不能以球员身份留下来,也要寻找一条留在篮球圈的道路。
“他一开始就冲着工作来的,”伊根回忆说,“他不是问我能不能干,而是告诉我他要去做。”
伊根让波波维奇坐下来,直言道:“这份工作并不光鲜亮丽。它有价值,但并不体面。”
伊根继续解释:这份工作和人打交道的部分跟篮球一样多。他将不得不离开亲人,一走就是好几个星期。这是一行残酷无情的行当——竞争激烈、毫不留情。伊根警告他,收入也不会多。但波波维奇并不在乎,他告诉伊根:“他不是为了钱。”伊根说,“他是为了学习这门事业。”
伊根以前也给别人上过这堂课,不少人听完都打了退堂鼓。但波波维奇没有犹豫:他志在必得。
不过在真正走上教练道路之前,波波维奇仍怀有打球的梦想。
1970年,他随美国武装部队篮球全明星队横跨东欧巡回比赛。1972年夏,美国奥运选拔赛在空军学院举行。当时的奥运选拔委员会成员小杰克·赫伦力推确保波波维奇得到邀请。刚刚退役并出任ABA卡罗莱纳美洲狮主教练拉里·布朗来到现场,看见了争夺12个名额的56名球员中的波波维奇。
“他一生都很专注。”皮尔斯说,“只是比我们那些疯朋友稍微没那么疯狂一点。”
波波维奇当时所在的选拔队由印第安纳大学教练鲍勃·奈特执教,但他最终没能进入大名单。
“这事快50年了,我至今耿耿于怀,”赫伦2016年说,“格雷格本该进那支队伍的。”
两年后,布朗成为丹佛掘金队主教练。1975年,波波维奇去掘金试训。
“我把他裁掉了。”布朗笑着说。
那时波波维奇也已经在空军学院担任伊根的助教,他的教练生涯才刚刚起步。
一开始,篮球对他来说是最遥远的事。波波维奇承认,没有任何大学向他发出过篮球邀请。他立志学医,灵感来自一位就读于瓦巴什的表亲。波波维奇甚至在校园参观时加入了一个兄弟会,他打算主修医学预科,只是顺便打一打篮球。
“没人招我,我只是打算去那儿读医学预科,然后顺便打打篮球。”他说。
计划很简单——跟随表亲的脚步,享受大学生活,也许还能在校队里混个位置。
“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去了空军学院。”波波维奇说。
他没有军人背景,家里也没有服役历史,甚至几乎不知道空军学院是什么。但有个同学曾被招到空军学院的预科学校;与此同时,还有两个同班同学正在被西点军校和空军招去打橄榄球。在他们的鼓励下,再加上老师和校长们对学院顶尖教育的极力推荐,波波维奇开始认真考虑这一条道路。
没多久,格雷格就开始填写国会提名表格,经历严格的申请程序。
“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我对那儿其实一无所知。但所有老师、校长都说这是最棒的机会。这是极好的教育,你应该去。我听了就说:好吧,那我就去吧。”
1970年,波波维奇以苏联研究学位毕业,随后服役五年。
无中生有
在他离开圣安东尼奥马刺队近半个世纪之前,波波维奇就曾因另一桩“交易”登上新闻。
1979年——在母校空军学院担任助理教练六年之后,年仅30岁的波波维奇被任命为庞莫纳-皮策学院的主教练。这则消息仅仅在加州寥寥数份地方报纸的角落里以小字刊登,或是出现在简短的新闻笔记里。
他来到的庞莫纳学院,是全美顶尖的文理学院之一,却只有区区1400名学生。规模之小,以至于在波波维奇上任前十年,该校不得不与附近不到一英里、同属克莱蒙特学院联盟的新兴自由派学院——皮策学院——合并体育部门。
尽管这些学院在学术上要求极高,但运动水平却因此受限。庞莫纳-皮策的球员不仅缺乏与一级联盟对手抗衡的身材和力量(这在三级联盟中属正常情况),更直接的问题是——他们的水平实在有限。波波维奇在1986年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甚至把自己执教的第一支队伍比作“校内俱乐部”。
“那支队伍里,可能也就四五个人在高中时当过首发,”波波维奇第一批弟子彼得·奥斯古德在2015年对 Grantland 回忆道,“大多数人连那个水平都够不上。”
因此,在波波维奇的带领下,庞莫纳-皮策的进步只能是缓慢、艰难而又曲折的。
1979-80赛季,也就是波波维奇执教的第一个赛季,“圣山鹧鸪”(是的,这就是他们的真实队名)仅取得2胜22负的战绩。最惨的一役,是输给了加州理工学院——这场失利不仅终结了对方长达99场的联赛连败,也送给对方在1971年至2011年间仅有的两场联赛胜利之一。
赛季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连完整的五对五训练都凑不齐——有人退队,有人因为课程繁忙无法参加。
招募球员的过程同样艰苦,却也是波波维奇乐在其中的挑战。那是远在录像集锦触手可及之前的年代,他会亲笔撰写长信,详谈候选人场上的目标与学业上的抱负;他会打电话询问他们的课程与家庭情况。
与此同时,他必须从极其有限的高中生群体中寻找人选——这些人既要能在赛场上有竞争力,又得具备进入庞莫纳或皮策这种严苛学府的成绩。相比之下,许多一级名校还会在录取上网开一面。当地高中教练偶尔会推荐人选,但常常南辕北辙:要么是场上明星却只有“B等”成绩,要么是天才学霸却连上篮都不稳。
尽管屡有挫折,波波维奇逐渐展现出日后为世人熟知的性格与风格。
执教初期,他和妻子、两个孩子就住在宿舍公寓里。他会在校园里散步欣赏艺术装置,和孩子们一起在食堂用餐,参加讲座,甚至主持了一个旨在废除校园兄弟会的委员会。他与教授们把酒言欢,辩论政治与哲学。
对球员们,他也像家人一般。他会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给家长写信夸奖孩子的表现;如果知道替补的父母到场,他会确保让他们的孩子上场。他还亲自帮一名学生经理竞选班长,在校园里贴满宣传海报——她最终胜选。他鼓励队员去支持校园里的其他活动,甚至组织他们在橄榄球比赛时经营小吃摊,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随着时间推移,庞莫纳-皮策的战绩逐渐改善。
从首赛季的2胜22负,到第二季的10胜15负,再到第三季在联赛中取得五成胜率。球队的轨迹明显向上,而这离不开这位年轻教练展现出的手腕与魄力。
在一次冷酷却高效的举措中,他让第一批队员全部重新试训,最终只有两人留下。他会招进超过需求的新生,只为增加发现“隐藏宝石”的几率。他还成立了二队,既补充了厚度,也建立了培养体系。短短两年间,球队的平均身高从6尺2升至6尺5。
他在技战术上的灵活与巧思,也因困境而被逼出。首年只能四对四训练时,他发现球队在场上少两人时反而打得更好,于是干脆把这种战术搬到比赛中:让四人进攻,一人滞留在中场附近,牵制对手防守;他们以“四外”阵型运转,没有人呆在禁区。一旦对手调整,他就让那名“游离”的球员伺机切入,令进攻从糟糕不堪变得勉强可看。
“他就像变魔术一样,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变好。”奥斯古德回忆道。
在招募上,他也偶尔淘到“金子”。比如来自河滨社区学院的6英尺5前锋戴夫·德塞萨里斯,他拒绝了数个一级校的邀请,选择了庞莫纳,最终打破了队史大部分得分纪录。再加上支持体育的管理层帮助,尤其是院长鲍勃·沃克尔——一位前三级联盟全美球员——的鼓励与支持,庞莫纳-皮策终于在1985-86赛季迎来突破。
凭借德塞萨里斯场均22分的带领,他们赢得了南加州大学际体育联盟冠军,这是球队68年来首次独占鳌头,并因此进入NCAA锦标赛。虽然最终被内布拉斯加卫斯理安以89比59大比分淘汰,波波维奇赛后表示“做梦都没想到会输得这么惨”。
但这支他称之为“一名天才加十个拼命三郎”的队伍,却完成了几年前无人想象得到的壮举。
“我们根本不在乎输掉NCAA比赛,”波波维奇对《学生生活报》说,“当然我们宁愿赢,但能拿下联盟冠军,我们太兴奋了,甚至感觉不到失落。”
在体育主任柯特·唐的鼓励下,他申请休假。不同于出国或暂离篮球以防倦怠,他选择向传奇教练们求学,换个角度观察篮球。
布朗始终记得他。1986年,当布朗成为堪萨斯大学主教练时,他打电话给波波维奇。他希望波波维奇能休假一年,作为志愿助教加入那支声名显赫的“杰鹰”队。波波维奇答应了。那支布朗的教练班子里,还有他日后在圣安东尼奥的合作伙伴R.C.布福德、未来的名人堂教练比尔·塞尔夫,以及未来的NBA教练阿尔文·金特里。
“波波是个了不起的贡献者,”布朗说,“我毫不怀疑他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教练。他关心孩子们,他渴望学习。他从不害怕表达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我们都因他而受益。”
在堪萨斯待了一年后,波波维奇回到波莫纳-皮策。一年后,1988年6月,布朗再次来电。此时布朗已经成为圣安东尼奥马刺的主教练,他想知道波波维奇是否愿意加入他的教练组。
“如果光看成绩,波波在波莫纳-皮策并不出色。”布朗说。“但问题在于,你要执教三级联盟球队的球员 ,或是空军学院的球员,本来就处于劣势。你得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培养球员上。而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天赋之一:他能让身边的球员变得更好。”
39岁时,在空军学院执教六年、波莫纳-皮策执教九年之后,波波维奇接受了布朗的邀请。
“很显然,这从NCAA三分之一联赛到职业赛场,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波波维奇在1988年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大概有五千个人都想要这份工作,而布朗至少认识五十个比我更合适的人。但他选了我。所以能得到这个机会,真的让我很受宠若惊。”
“这是一次相当大的飞跃,我很高兴,”波波维奇说,“但同时,我也吓坏了。”
布朗观察到,波波维奇执教时很严厉,但懂得把握分寸。
“他最大的优点是明白执教和批评的区别,”布朗说,“在他手下打球,你可能会被骂,但你知道他是在关心你。这一点我一直坚信。最伟大的领导者,不论在哪个领域,都是真心关心他们所领导的人,而被领导的人也能感受到这种真心。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当球员们知道你真的关心他们时,不管他是谁,他们几乎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对于庞莫纳-皮策,波波维奇短暂离开期间环境已然改变。他的好上司沃克尔去世,新领导层对体育的热情不再。1987-88赛季结束后,心灰意冷的他开始思索离开这里,另寻他处。
1988年夏天在木屋度假时,波波维奇听闻布朗在率堪萨斯夺冠数月后,被任命为马刺主教练。助手李·温伯利建议波波维奇打电话求个机会,但他担心布朗会损他一顿。
“他觉得布朗会当面笑掉大牙。”温伯利后来回忆。
只不过事实完全不同。波波维奇随布朗前往圣安东尼奥执教四年,又到金州勇士跟随唐·尼尔森两年,最终于1994年回到马刺,出任篮球运营总裁兼总经理。
然后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故事了。
苦乐参半的回乡
自波波维奇离开后,他的家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加里市曾因成为迈克尔·杰克逊和杰克逊五兄弟的诞生地而名声大噪。但与此同时,美国钢铁工业的衰落已让这座城市走向没落。
曾经雇佣三万人的加里钢厂,如今只有四千名工会工人。
加里的人口从1960年峰值的178320锐减了55%,剩下的居民生活在全美最贫困的城市之一。
在往日热闹的百老汇大街,如今关门的商铺多于营业的。
那块曾让波波维奇历练坚毅的露天球场,现在有一半被快餐海鲜店占据。旁边的小学废弃多年,如今被一家创业化工供应公司使用。
不过这种贫困程度尚未蔓延到梅里尔维尔。这里依旧是印第安纳西北部主要的零售中心之一。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梅里尔维尔人口已涨至35246人,比2000年增长了14%。波波维奇上学时,梅里尔维尔高中只有约800名全白人学生。如今学校人数已达2300人,其中83%是少数族裔,大多数是黑人。
尽管波波维奇已成为世界公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伊斯坦布尔都能如鱼得水,但骨子里,他依旧是梅里尔维尔的工薪子弟。
“很多人会忘记自己的根。”梅里尔维尔高中的体育主管贾尼斯·夸利扎说,“可他不是那样的人。”
2005年,在带领马刺夺得第三个总冠军几个月后,波波维奇回到梅里尔维尔的体育馆,学校为他退役了21号球衣。那天海盗队正对阵劲敌皇冠岬,全场座无虚席。
波波维奇带着一个来自早已关门的加里裁缝店的衣袋,里面是他1966年的蓝白校队夹克。
当他把夹克穿上,全场沸腾。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居然还合身。”帮忙组织活动的贝克汉姆说。
虽然夸利扎和贝克汉姆在梅里尔维尔学区已工作二十多年,但在那之前都未曾见过波波维奇。那天他们印象深刻:刚刚率队夺冠的主帅,在梅里尔维尔依旧自在如常。
他看完了整场比赛,还留下来一个小时签名、握手。之后与老教师、老朋友,还有一些久未谋面的熟人一起小酌畅谈,其中不少人还是他当年在加里打野球时的伙伴。
那是个让小镇和它最著名的儿子共同动容的夜晚。体育办公室里至今还挂着当时的照片,照片中的波波维奇笑容灿烂。
“他为自己是海盗队员而自豪。”夸利扎说,“这对我们意义重大。”
波波维奇的老数学老师,则从另一角度看待他与梅里尔维尔的关系:
“谁能想到,一个来自梅里尔维尔高中的孩子,会成为全国第一的教练?”哈钦森说。
波波维奇本人当然不会。
球衣退役仪式后,贝克汉姆记得他仍在笑着感谢自己,并补了一句: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退役了我的球衣。我那时候可烂透了。”
这些回复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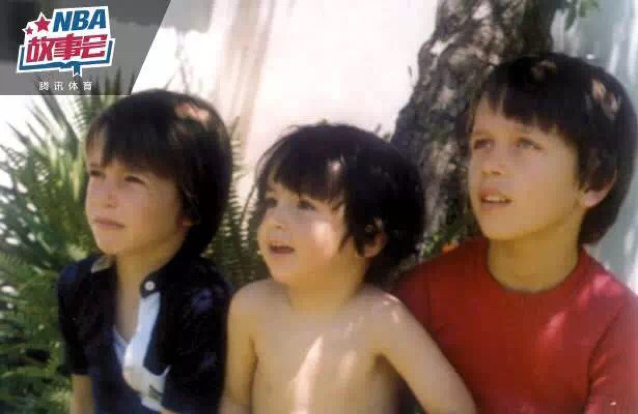
ATT球场的蝙蝠
刺区没有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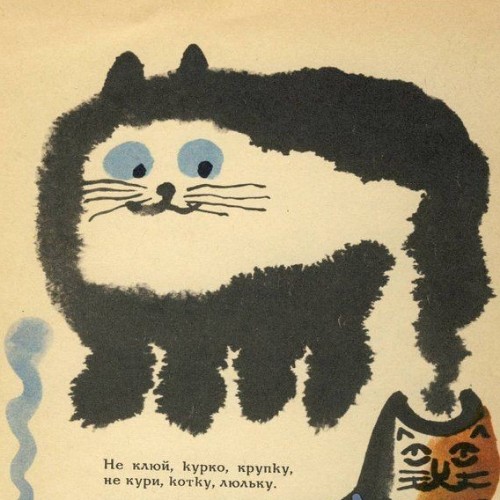
菠萝面包白
· 北京感谢作者,我们对波波以前的故事了解的可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