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搜我想看
搜我想看【球星看台】布歇: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在蒙特利尔,露宿街头是可能会被冻死的。
所以,我16岁无家可归的时候就会这么干:
蒙特利尔有一条穿过整个城市的公交线路——380路亨利-布拉萨线。
它从我长大的蒙特利尔北部出发,一路开到城市西边,沿途停靠许多站点。它没有末班车,整晚都一直开,从起点到终点通常要两个小时。
我晚上会待在这辆公交上,而这两个小时我会被冷到只有脚趾还能有知觉,身体的颤抖只能通过咬住舌头来缓解。
那时候,白天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赚公交费,一旦夜幕降临,寒风呼啸而过,无论我在哪,我都会立刻直奔公交站。
当380路前面的车门缓缓打开,我健步如飞地上车,掏出2.75美元车费,然后找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然后…
闭上眼睛。
有时候我实在累得不行,疲惫会直接将我带入梦乡,我张着嘴口水流到脸上,睡得十分沉。有时候我没累到直接能睡着的地步,我就会开始闭上眼睛幻想着一些积极的事情发生,我幻想着我的家人们可以重归于好,幻想着有一天能够中彩票,幻想着命中一连串三分球,或者任何美好的事情。
有些夜晚这两个小时感觉就像永恒,有些夜晚又感觉像两分钟一样短暂。公交车驶入车站,随着刹车声一响,我的脖子也会急促地向前倾。
这就像是闹钟一样。
两个小时到了。
我踉跄着下车,坐在车站的长椅上等30分钟。这是司机固定的休息时间。他通常会抽一根烟,或者喝一杯咖啡,上个厕所之类的,然后继续上车。
我总是跟在他后面的第一个乘客。
然后再掏出2.75美元车费。
坐车回到两个半小时前我出发的地方。
返程的路上,我会再睡一会,或者听听音乐,或者看着窗外富人区里停着的一辆辆豪车。
当我再次回到北边时,四个半小时的夜晚时光终于被消磨完了。
如果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5.5美元,我会再重复一次。坐两个小时车,和司机一起下车半个小时,然后再坐回来。像这样一个冬夜我找个地方睡觉需要11美元。
每个晚上都处于无尽地循环之中。
每晚,同样的司机都会驾驶同样的380路和同样的少年走过同样的路线,那个少年总是枕着同一件外套。每晚都是如此,雷打不动。
夜复一夜。
那个身处无尽循环中的少年,他看不到任何出路。
五岁那年,我跟着母亲从圣卢西亚来到蒙特利尔。 年幼的我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离开小岛。我的父亲和弟弟已经在加拿大住了一段时间。我和母亲希望尽快能和他们相聚,这是我当时依稀记得的,现在也只有残存的记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一天前我还在小岛上的山区里住着,隔天我就到了加拿大第二大都市。
而这里也太特么冷了。
初到蒙特利尔之时,我们住在一栋不错的两层楼里,是爸爸和姑姑此前落脚的地方。那是在Pie第九街区。这里的社区很棒,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我弟弟比我小一岁,我们很快变得形影不离。我们会滑雪、滑冰和堆雪人,每天玩得不亦乐乎。节假日到来之时,我们会和邻居一起举办家庭聚会,大家载歌载舞。
七岁之时一切都变了。
我的父母当时经常吵架,他们对着彼此大喊大叫。一次圣诞节,我听到他们在谈论卖房子的事情。 在我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时,父母就分开了。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搬到了一间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在Nord街区,跟之前的社区完全不能比。
为支付房租和买食物,我母亲白天在食品店打工,下班后又赶去加油站的便利店上夜班。身为老大,她不在时我必须照看弟妹,这意味着晚餐要由我负责煮泡面。那时候我基本把那些预制菜热一下——芝士通心粉、或者肉酱千层面,我妹妹特别爱吃这些。但除了比弟弟妹妹会用微波炉之外,我根本不像个哥哥。那时我也才九岁或十岁,也只想到处乱跑和玩。
问题是,我们住的地方治安不太好。
这里每天警笛声日夜不绝于耳,枪声也时常响起。那些熟悉的面孔,可能前一天还在身边,第二天就永远消失了。
所以妈妈上班时,她不让我们离开公寓楼前门半步。多数时候我们都窝在屋里玩GameCube上的《马里奥赛车》《任天堂明星大乱斗》或《马里奥派对》。
但随着我渐渐长大,我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必然的。而当我真正踏出家门时,眼前的一切完全印证了母亲的警告。
这里毒品无处不在,黑帮的暴力冲突持续不断。虽然我并未加入帮派,但只要生活在他们的地盘上,无论愿意与否……我的安全在无形之中已经受到了威胁。 那年夏天,我已上高中,在公园参加年度街头篮球赛。所有人都心知肚明——11点钟一到,灯光就会熄灭。某晚我们队打半决赛,时近10点45分。我站在球场上焦灼地盯着时间,因为熄灯时刻将至,而之后……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突然间,场景如同电影情节般展开。
我们耳边先是传来照明灯逐个关闭的声响。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紧接着:砰、砰、砰、砰、砰、砰、砰。
听起来像放烟花,实则是枪声。
所有人四散奔逃,尖叫着狂奔。
但说来奇怪……我竟毫无惊慌。
没有恐慌,没有像无头苍蝇般乱窜。
那一刻我内心毫无慌乱,唯有专注。
因为到那时……我早已习惯这类疯狂事件。
它们成了我的日常。
真正改变我的是意识到无法再和母亲同住的那天。
当时我们寄居在她男友家。但我和这个男人格格不入,相处得很不愉快。那时我正值青春期,十六七岁,为了帮家里赚点钱辍学打工。打工之余,我总在外面打球,几乎从不回家。
某晚与母亲交谈后,我们达成共识:为了弟弟妹妹有个安身之所,也许从这离开才是我最好的选择。
那次对话将我带入前所未有的迷茫。
那一刻,仿佛我的生命力瞬间从身体里被抽离。我在精神上从未如此低落。
该死,我知道我必须保持清醒和冷静,但此刻我真的感到彻底被抛弃了。
然后……我只能流落街头了。
不过说真的,我不会真正无家可归。至少不是完全如此。
当时原计划是每晚轮流住在我爸和姑妈家。但现在回想起来,这根本不是个好主意。
父母离婚后,我们每隔一个周末才能见到父亲,而这种安排似乎总让他倍感压力。仿佛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把我们送回去。
十六岁离开母亲家时,母亲提议让我偶尔住父亲那里,他立刻开始纠缠母亲要求抚养费——企图借我住在他家的机会追回部分抚养费。后来试住几晚后,父亲竟要求我付房租、承担他的网络费之类开销。
没过多久他就直截了当地说:“这完全不是我希望的。你不能住在这里。”
至于姑姑家,虽然她收留我可能救了我一命……但这种安排同样难以维系。每次住在那儿都能感受到屋里的紧张气氛。他们约朋友来玩时,我总像个局外人被晾在一边。后来我明显待不下去了,他们会主动说:“行啦,今天够了。你得走了,过几天再来吧。”
这种时候我就得动脑筋。有时我会溜到父亲家,等他出门上班后潜入屋内,在沙发上蜷缩片刻,再趁他快到家时溜走。
那时多少个夜晚,我独自伫立在某条街头,夜色渐深,寒意袭人,只能茫然自问: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那些无处可去、又没钱坐380路公交的夜晚,我只能走到哪儿是哪儿了。
这通常意味着我的步数都爆表。
这不是那种饭后愉快的散步。也不是锻炼身体。我说的是为了消磨时间而走的路。为取暖而不得不行走。那种行走是孤身一人,面对寒冷而黑暗,只是漫无目的地游荡,只为不必露宿街头。
有时行走途中会撞见通宵营业的麦当劳,我会进去休息,直到被店员赶出来。然后我又回到寒夜中继续行走。我必须坚持下去。必须挺过去。我别无选择。
记得我会自创一些无聊的小游戏,只为保持头脑活跃,或是强行找乐子。比如:冲到下个红绿灯,跳起来拍街牌。或是:跑到下个灯,走过下一个,再跑下下个。我从不会刻意计算自己走过的距离,但抬头时总会惊叹自己竟走了这么远。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用我的脚步丈量了整座城市。那些夜晚,我总在街头漫步数英里。但实则却始终在原地踏步。
我始终尝试着积极看待发生的一切。
于是,该说不说…夜间漫步确实提升了我的心肺功能。
我精力充沛,在篮球场上能如飞鸟般不知疲倦地穿梭。但说实话,我在篮球路上真正的转折点,是我终于学会了扣篮。
直到十六七岁时,我总觉得自己浪费了身高优势——我像个徒有其表的巨人,毕竟我当时身高6尺8寸,居然不会扣篮。我多年来尝试各种训练技巧,却始终毫无进展。
后来我不得不暂停扣篮练习,纯粹因为太过沮丧。我转而专注练习三分球,开始和城西一群菲律宾人打球,他们教我各种投篮训练。每周二三五固定在球场训练,渐渐成了习惯。我严格遵守训练计划,投篮水平很快提升。
但扣篮依然无望。
直到某天,不知怎的好像有人对我施了魔法一样,我突然开窍了。当时,我在球场随意投篮时突然停手,一股冲动席卷全身:我现在就去扣篮!
我助跑起跳,虽然明显走步了,但当我跃向篮筐时,球没有撞框,我也没有在空中失控——我…… 真的扣进了。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超级英雄,仿佛无所不能。 我立刻再来一次。接着又一次。
短短两分钟内,我的心态从“不可思议”转变为“也不过如此”。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纯粹是想多了。你只需要让身体接管大脑,然后纵身一跃就够了。
自那之后,天啊……整场比赛我都在别人头上扣篮。无人能挡。
但请记住:我当时辍学了。这些比赛都在户外的沥青球场进行。这可不是在高中体育馆里当着各路球探的面扣篮。
我是在游乐场旁的秋千架和滑梯旁,和一些成年男人打街头篮球。我当时压根没想过职业篮球或进NBA的事。
幸运的是……似乎只要在你扣篮的次数够多,无论你在哪打球,球探们都会找到你。
学会扣篮不到一年,阿尔玛学院的教练就看到我的比赛,邀请我加入他们的AAU球队。不久后,我便远离家乡坐了五小时车,前往他们的预科学校学习打球。
阿尔玛学院的每个人都给予我极大的支持。我再也不用担心每晚睡在哪了,这感觉真好。这种转变带来的改变难以言喻,尤其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摆脱诸多烦恼后,我得以全身心投入训练,我的篮球技术也进步神速。
全美多所高校向我抛出橄榄枝,但因中途辍学,我的学习成绩无法让我进入一级联盟院校。最终我先在新墨西哥州读了一年社区大学,又在怀俄明州读了一年。我打出了堪比电子游戏的惊人数据,荣膺全美社区大学年度最佳球员。
一切都在飞速发展。
某天我回过神来……发现夜里不用在经历刺骨寒冷,我的三餐不再只有泡面,而我坐的每趟巴士终点都是体育馆——那里总有人专程来看我打球。
2015年5月15日,我正式承诺加入俄勒冈大学。那以后,我在篮球场上的所有表现都出现在了电视上。
刚到俄勒冈大学不久,整个校园的人都认识我,他们纷纷向我打招呼问候。那感觉简直超现实。
在赛场上,我开始迎战更高水平的对手,而且表现出色。我完全进入状态——飞身封盖、三分命中、奔跑无阻。转眼间我们打进了NCAA锦标赛,球队实力强劲。
我们队里聚集着众多未来的NBA球员——狄龙-布鲁克斯、佩顿-普里查德、乔丹-贝尔——而我也在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这简直像美梦成真。
在蒙特利尔北部长大的我,绝对没想过未来会有这样的际遇。
但俄勒冈生涯的终章,绝非迪士尼电影般的童话结局。这并非流浪少年一夕成名、从此顺风顺水的剧情。我并未因跻身顶级大学篮球圈就一路高歌猛进,更没有活出完美人生。
就在参加选秀前的Pac-12联盟锦标赛上,我撕裂了前十字韧带。当时还不确定具体伤情,只是在争抢篮板落地时姿势扭曲,瞬间感觉不对劲。那场比赛我几乎单腿撑完了全程(至今不知我如何做到的)。
次日我进行核磁共振确诊——前十字韧带撕裂。需要手术治疗,预计休养九到十二个月。就这样,我从选秀热门、潜在首轮秀沦为落选球员。
老实说,那段日子我确实陷入了低谷。当时我所在的大学球队排名全美前十,我们正在备战NCAA锦标赛,我本该迎来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结果却被迫因伤休战。
我不仅需要错过锦标赛,更要缺席整个下赛季的大部分比赛?!更何况我已经24岁了,比NBA新秀平均年龄大得多。现在还遭遇前十字韧带撕裂?!哪支NBA球队会要这种球员?!
那段日子里,我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
但……我依然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像从小到大那样,继续迎难而上。
或许我本可以放弃。回到家中另谋出路。但我从未动过这个念头。我始终坚信自己,拼命康复训练,让篮球技艺更上一层楼。纵然前路未卜,但我坚信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2017年选秀夜,勇士队同意与我签下双向合同——即便当时我还在康复前十字韧带伤势。那一刻仿佛终于冲破重重阻碍,迎向光明。
我清楚自己将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我渴望在联盟中崭露头角。我坚信一切付出终有回报。
几周后,我就火速出现在了勇士训练馆里练习投篮,而我身边是库里、杜兰特和汤普森,我得以向顶尖中的顶尖球员学习。
当我伤愈复出,在对抗训练和练习赛中能与他们打得有来有回时,我确信自己有能力站稳脚跟。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只是时间问题。
但正如我所说……现实绝非童话故事。
尽管我确信新秀赛季定能震撼NBA,结果是我想多了。
我简直大错特错。
或许早该明白事没那么简单。不过话说回来,那可是2017-18赛季的勇士队——我们的阵容堪称史诗级。但事实就是……
那赛季我为勇士队出场时间仅有一分钟。
就一分钟。
那一分钟我做了什么?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忆犹新:抢到一个篮板,然后投了一个三分,三不沾…
随后在季后赛前夕,勇士队决定裁掉我。
如今回想起来,尽管收到通知时很沮丧,但某种程度上这反而帮了我。
它让我意识到能成为NBA球员是何等幸运和不易,也让我更决心向世界证明自己。
当时我心想:哦,该死。就这样?我居然就这样被联盟淘汰了?我不断告诫自己绝不能沦为那种50岁还在街头球场打球,然后靠这种潦草的经历就吹嘘自己“曾经打过NBA”的家伙。
我不想成为那种说“我在NBA打过球……”然后不得不补充“就一分钟”的人。这让我心中又燃起了一团火
但最疯狂的是,勇士队裁掉我时并未立即公布。季后赛开始前几天,他们给我买了头等舱机票送我回家,但直到总决赛结束近两个月后才对外宣布。
我记得自己踏上了旧金山飞蒙特利尔的红眼航班,在肯尼迪机场转机时,黎明时分坐在纽约机场的场景相当震撼——我不禁问自己,我该何去何从呢?
某一刻我抬头,竟遇见了我的经纪人萨姆,他恰巧也在当天早晨起飞。
我们坐下吃了两个小时早餐,聊起发生的一切:我的职业生涯、被裁的失落感,以及下一次机会的重要性。我知道留给我的机会已经不多了。若不能继续展现实力让人印象深刻,我将被发配到发展联盟或海外联赛——很可能就此终结职业生涯。这是决定我篮球生涯成败的关头。
记得当时我边吃着煎饼喝着果汁边告诉他:我已准备好迎接任何机遇,无论任何球队抛出橄榄枝,请务必帮我接住。
回到家乡后,接下来的几个月异常煎熬。人们仍以为我是勇士队成员。我不敢告诉任何人自己被提前裁掉的事,生怕消息走漏影响下次机会。
回到蒙特利尔后,我几乎足不出户。说白了就是在躲藏——整整两个月,我像个逃犯似的躲在母亲家里。
我和母亲、哥哥、姐姐一起打开电视,整整两个月,看着我刚刚效力过的球队——一支历史级别的强队——一路杀入NBA总决赛,最终横扫克利夫兰夺冠。
记得第四场结束后,母亲见我情绪低落,说了句当时听来简直疯狂的话:
“别担心,克里斯。明年举起奖杯的会是你!”
这话听着很暖心,但当时的我只能……
是啊,妈妈,当然啦。完全没问题。行吧,您说得对。
能在多伦多夺冠,又幸运地在加拿大度过七个精彩赛季,对我意义非凡。我想,这才是我真正的迪士尼式结局哈哈。当然过程并不轻松——我从夏季联赛特邀球员起步(前两场还被雪藏),努力争取到训练营合同,继而获得双向合同,成为G联赛史上首位单赛季包揽MVP与最佳防守球员的球员,最终才签下首份标准NBA合约。之后便是日复一日的拼搏和努力。
我无比感激猛龙队给予我的机会——在我以为无人相信我时,他们再次给予我信任。从总经理乌杰里,到工作人员、教练、训练师、保安,球队里的每个人。他们都待我如家人般接纳包容。这份情谊弥足珍贵,我将永远心怀感激。
自从我从圣卢西亚来到这里,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但我深爱着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人民始终给予我关爱与支持,若没有来自加拿大各地不同人群的帮助,我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自己。
必须说:我最欣赏加拿大人的一点是……说不清具体原因,但许多人……天生就……充满乐观精神。
他们总能看到事物的积极面,无论当下处境多么艰难,他们总是相信转角处必定有光明等待。他们对此坚信不疑,总是从容应对人生起伏。
这太酷了!
这种视角无疑是我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它让我在年轻时充满不确定性和动荡的生活中持续前行。从小我就对拥有的任何事物心怀感激,即便几乎一无所有时亦是如此。我从未停止微笑,从未停止相信自己终将迎来转机。一次都没有。
这份信念我至今仍珍藏于心,并通过SlimmDuck基金会努力向他人传递。我们的目标是为儿童和弱势群体创造有意义的机会与体验,并提供他们成功所需的工具。例如提供学习用品、奖学金、免费篮球训练营、餐食、节日礼物等。这些工作令我无比自豪,但最令我骄傲的是通过基金会及合作伙伴为青少年提供的心理健康支持与导师计划。我深知心理与情绪挣扎的滋味,明白它对人的摧残。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分享这段人生旅程中的领悟,以此促进身心健康、自信心与韧性——尤其要惠及年轻一代。
我感觉自己太幸运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是如此幸运。在很多方面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我始终努力奋斗、保持积极心态、从未放弃对自我的信念,这些年来才得以经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时刻。
赢得NBA总冠军是一回事……
但夺冠后能把奖杯带回加拿大?
尤其是经历了所有人生磨难后夺冠?
这种感觉难以言表。
就像……
我曾经整夜辗转于公交车上只为有个地方能睡觉,而不至于冻死在街头。
如今我站在车顶高举NBA奖杯,作为冠军,我们穿过多伦多市中心,drake为我们高声助威…
更难得的是,我从这里为我的nba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效力于多伦多,为加拿大球队效力,这意义非凡……
有时我不得不掐自己一下,确认这一切不是梦。
这些年我始终是猛龙队的一员,从菜鸟成长为联盟老将。而如今我将为篮球界最具标志性的球队之一效力。我期待穿上凯尔特人的绿色战袍,再次向世界证明自己,为总冠军而战。我希望从今天开始能将另一个地方称之为家,我会继续每天努力训练,打我热爱的篮球。
这一切该如何形容?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始终坚信:明天永远会比今天更好。
明天,我会努力凑齐11美元,争取睡个安稳觉。
明天,我会完成扣篮。
明天,明天……
一切都会好起来。
明天,我会有床可睡。
我会有家可归。
我会安然无恙。快乐、健康、心安。
所以,是啊,虽然我无法解释这一切。但有一点我确信:只要保持积极,坚持信念……无论处境多么艰难,兄弟,我发誓……
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全部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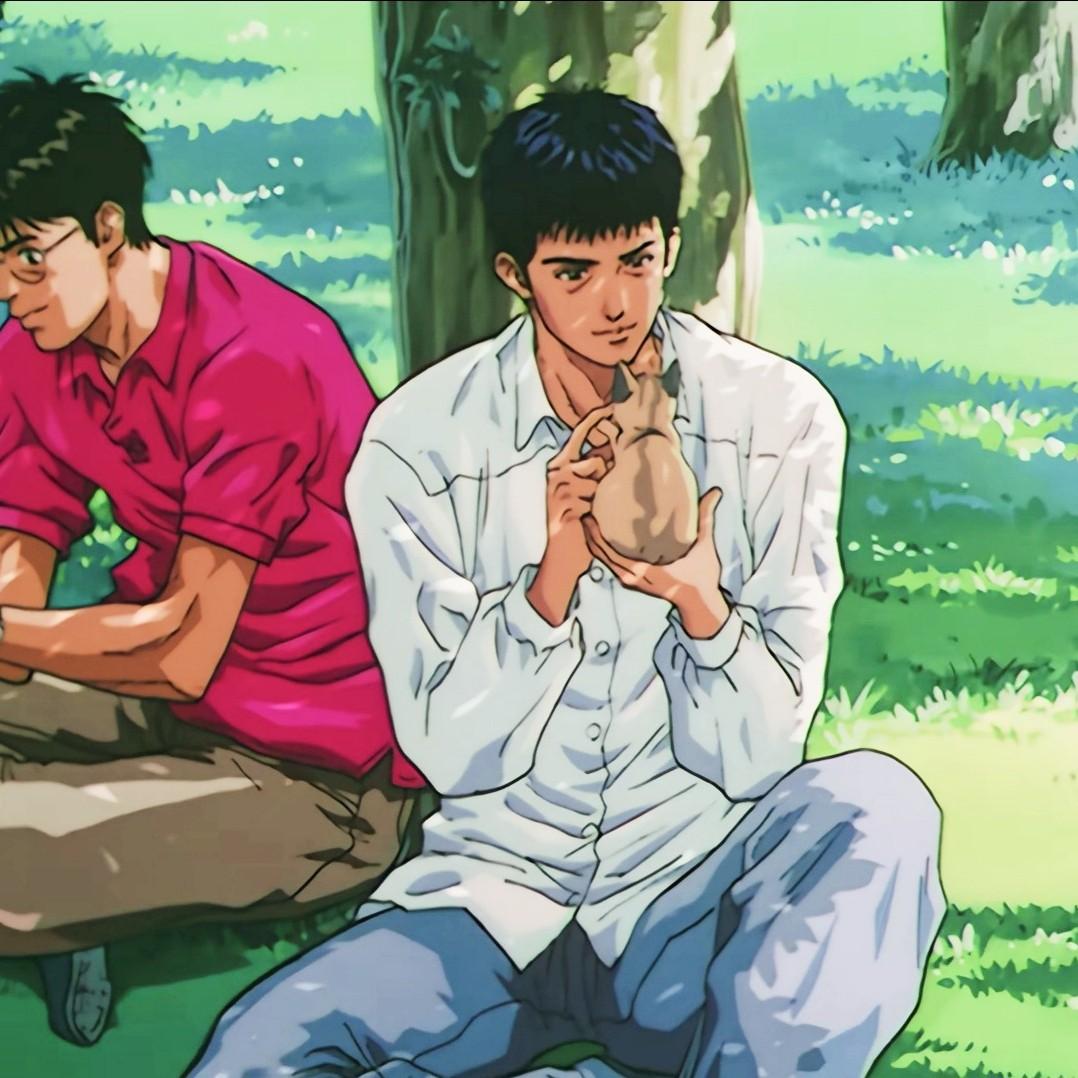
丹尼安吉的来电
· 浙江
老许哈哈哈
· 河南